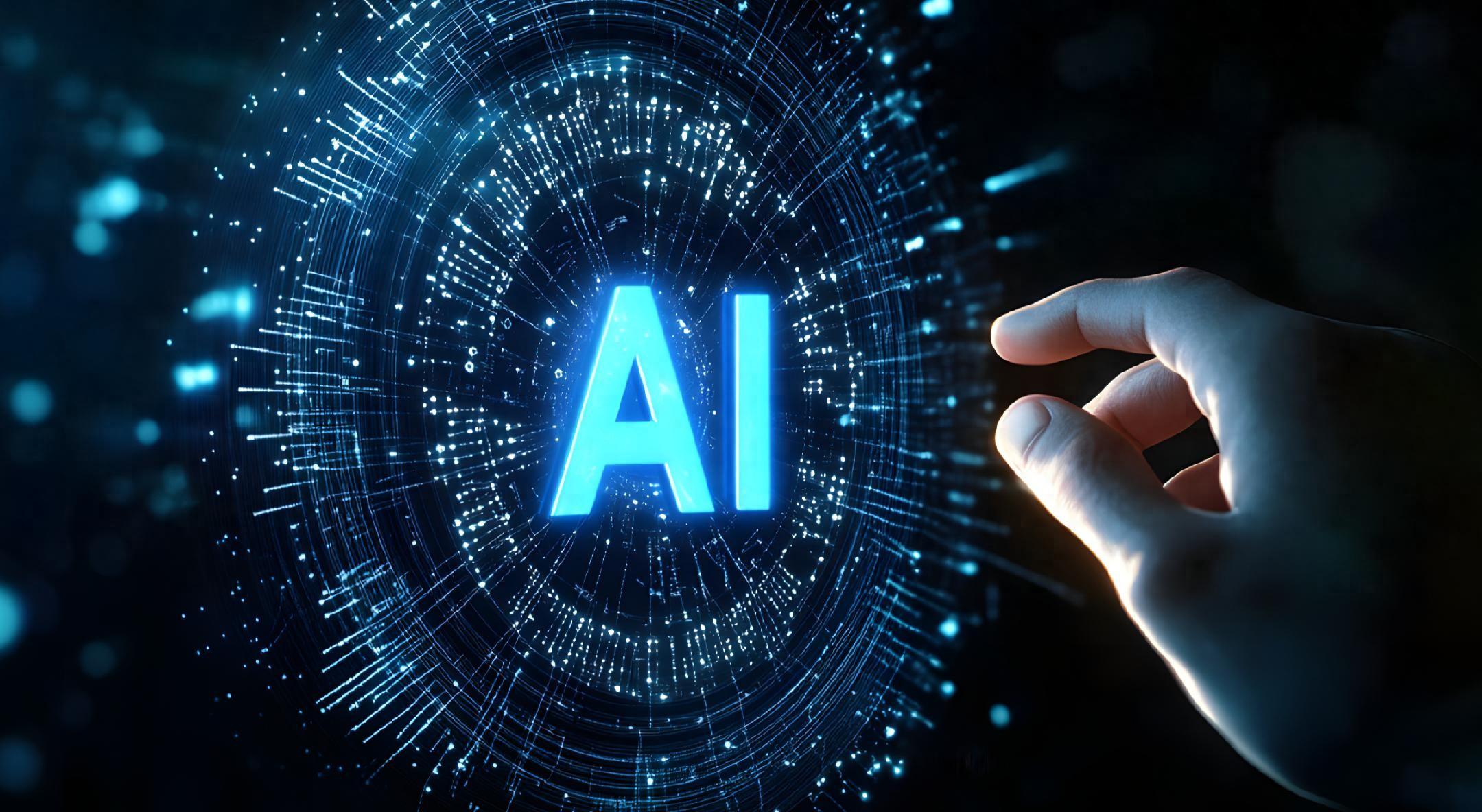文 | 新聲Pro,作者 | 安濟
2024年,耄耋之年的袁和平坐在新疆戈壁的導演椅上,風捲着沙礫掠過監視器,電影《鏢人》開機。一年多後,81歲的袁和平從片場走到了今年春節檔競爭的戰場。
這部脫胎於現代漫畫的電影,集合了李連杰、吳京、謝霆鋒、張晉、梁家輝、惠英紅、於適等,演員名單幾乎覆蓋了華語動作演員譜系中所有尚在活躍的代際。《鏢人》的氣質是複合的。原著漫畫雖以凌厲畫風和「硬派」風格著稱,但其精神血脈既接續着傳統武俠的俠義倫理與家國情懷,又糅合了西部片的孤絕美學與日本劍戟片的凜冽刀鋒。
這種「古典內核與現代語法的交融」,使得電影的成色指向一個關於武俠精神在當下何以爲續的問題。袁和平是這個問題恰當的提問者,被稱爲「天下第一武指」,也幾乎是武俠電影江湖最後的「連接點」:其父袁小田是香港電影最早的武術指導之一,而他本人親歷了從李小龍到成龍、李連杰、甄子丹,再到吳京的每一次潮汐更迭。
憑藉「硬橋硬馬」的真實感成名,袁和平也在好萊塢用《黑客帝國》《殺死比爾》等影片證明了功夫作爲純粹視覺奇觀,能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的魅力。他口中「俠義精神」是武俠之魂,但滋養那份精神的古典江湖與現實土壤,正在飛速消逝。
因此,《鏢人》驗證的不是一部古裝武俠片在今天能有多賣座,而是當徐克以《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重述家國俠義卻反響寥寥,當徐浩峯用《師父》《刀背藏身》將武俠解構爲冷峻行業圖景,反而成了「小衆影片」,一種更現代、更漂泊、契約式的「俠客」形象,是否還能與袁和平所代表的,過去的時代基於真實肉身技藝的動作美學成功嫁接,並打動觀衆。
在時代轉換的縫隙中,故事或許可以從那個「功夫」與「江湖」尚且彼此篤信的年代開始追溯,直到締造過武俠片輝煌的行業體系逐漸遠去,「俠義」的古典內核遭遇現代語境的疏離,真實「功夫」在特效中逐漸隱身,再去追問,今天的武俠電影,究竟站在何處。
「舊江湖」的星辰與門派
真正的江湖,從不屬於一人。袁和平的出現或許應該放置於那個羣星璀璨、門派林立的「武林」中去理解。那裏並非某個人的舞臺,而是劉家良、洪金寶、成龍與袁和平,共同構建的「四大家班」鼎立格局。
袁和平的「伯樂」之名,源於他能爲不同的「武術身體」找到銀幕語法,這背後是一套精準的「適配」邏輯。他將成龍的戲曲功底化爲《醉拳》中頑皮詼諧的雜耍,將李連杰全國武術冠軍的英氣,淬鍊成《黃飛鴻》系列裏大開大合的宗師風範,又把甄子丹的現代搏擊感,融入《鐵馬騮》疾如閃電的狠厲實戰。

如多年後他總結的那樣:「我其實是看人物性格怎麼樣,我根據人物性格設計功夫、設計動作。」動作若不配合人物性格,便是無源之水。但這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背後支撐的是一個健康、繁榮甚至狂野的行業生態:從於佔元戲班裏摔打出來的「七小福」,到各省市武術隊裏儲備的精英,源源不斷的人才如活水般湧入;嘉禾、邵氏等製片廠敢於冒險,爲創新押注;而整個亞洲市場,都渴求着下一個令人血脈僨張的新口味。
那時的江湖,各有清晰「武學」路數。劉家班的劉家良,是黃飛鴻正宗洪拳傳人,一招一式講究南派武術的正統與紮實,力主「真功夫」,反感飛來飛去。成家班的成龍,則將搏命特技與市井喜劇融爲獨一無二的個人印記,從鐘樓躍下、商場燈管滑落,每一次「玩命」都刷新着動作的視覺和心理極限。洪家班的洪金寶,身形龐大卻異常靈巧,集詭異、幽默與剛猛於一身。而袁家班的袁和平,則以兼容幷蓄與清晰的招式教學感著稱。他像一位最懂觀衆心理的解剖學家,把複雜的武術拆解成好看、易懂又充滿趣味的電影語言。
彼時江湖武學門派之間,是激烈的競爭,更是互相的滋養與激發。正是這種高烈度、一體化的封閉性競爭,鑄就了香港電影征服亞洲、乃至讓好萊塢側目的硬核競爭力。影評人、紀錄片《龍虎武師》導演魏君子,曾用八個字概括那個時代:「盡皆過火,盡是癲狂」。這原是外國影評人的揶揄,卻成了對港片蓬勃生命力最精準的註腳。
在這個江湖裏,袁和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不是唯一的星辰,卻是懂得如何讓不同星辰綻放異彩的那個人。然而,這片璀璨的星空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劇變的暗流也在湧動。

遠行的遊子,失語的故園
江湖的消散,始於最精銳力量的遠行與內部根基的悄然鬆動。這種鬆動並非一夕之間,背景是九十年代末香港電影在亞洲金融危機、本土市場萎縮及人才外流等多重衝擊下的整體困境。影人北上或西進,成爲尋找出路的普遍選擇。
1998年,袁和平受其「粉絲」、《驚世狂花》導演沃卓斯基的邀請,遠赴好萊塢,爲《黑客帝國》設計動作。這堪稱一次完美的「文化轉譯」,他面對的是對東方功夫充滿熱情卻毫無基礎的西方演員,方法是迴歸傳統與基礎:讓基努·裏維斯等主演進行長達四個月的體能、基本功和吊鋼絲訓練。
最終,那些「鷹展翅」、「鐵板橋」的經典鏡頭,將中國武術的形態精粹爲全球觀衆驚歎的「視覺奇觀」。雖然國外的觀衆,因爲這當中有地域文化、種族階層、個人情趣品位多方面的侷限,並不能理解武術與故事情節和表達之間的內在關聯,但合作的成功,建立在袁和平自己對「東方功夫+西方特技」的理念深感興趣,以及與導演對動作「真實性」的共同追求上——即使這種真實是服務於一個科幻故事。
但這種成功同樣是一種「文化抽離」。中國功夫的哲學、倫理及其賴以生存的、講求忠孝節義與師徒恩仇的「江湖」人情世故,在虛擬世界的子彈時間裏,被簡化爲了純粹的動作美學。功夫以此征服世界,卻也與它的文化母體悄悄斷了臍帶。對此,袁和平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爲進軍國際的關鍵在於「人性」與「國際化的劇本」,「如果只講什麼門派,外國人不瞭解,就沒辦法進入。」
當「袁和平們」在海外重新定義「中國功夫」的全球形象時,本土的江湖卻加速荒蕪。市場萎縮、片廠制式微,最致命的是傳承鏈條的斷裂。過去那個從龍虎武師、武術指導到導演的完整梯隊培養體系,隨着行業蕭條而瓦解。

袁和平曾在公開採訪裏感慨:「香港沒人學了,真的沒人學功夫,因爲生活條件不一樣了,生活條件太好了,學功夫太苦了,不如讀書學別的。香港武術電影好像後繼無人了。」他將原因直指核心:無人發掘。
過去,他可以去武術隊、舞蹈隊憑經驗「選材」,如今,這套機制幾近停擺,甚至對兒子是否學武也持開放態度,因爲「太苦了」。「武術這個行當,真的要當它是一個事業就比較難,最好的環境就是在武術隊做教練,拍電影就很難出頭了。」
與此同時,武俠的美學內核也在激盪中駛離原本的方向。徐克等導演以數字特效將武俠引向更爲瑰麗奇幻的想象,而袁和平所代表的那種倚重肉身苦練、追求物理碰撞真實的「硬橋硬馬」風格,顯得日益「傳統」。他曾在拍攝3D電影《蘇乞兒》時強調:「用2D拍我可以‘偷機’……但是3D有兩個鏡頭,就不能偷接,一定要打過去,拳拳真的到肉。」這種對真實感的依賴,與技術驅動的奇觀化潮流形成了微妙對峙。
更深層的危機,在於「俠義」精神的懸浮與失語。金庸筆下「俠之大者,爲國爲民」的宏大敘事,其情感基礎是家國一體的倫理觀念。而在當代個人主義與解構主義盛行的語境下,這種敘事與年輕一代產生了隔膜。
2025年徐克執導的《射鵰英雄傳:俠之大者》在票房與口碑上的雙重失利,便是一個刺眼的例證。該片既未能在視覺上覆現導演巔峯期的想象力,也未能讓當代觀衆對「俠之大者」產生情感共鳴,口號最終懸浮於故事之上。
袁和平自己也曾指出拍攝現代俠義故事的困境:「拍現代,很多禁忌在那裏,也可以拍,但是審批又有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拍,還是拍以前的故事,比較容易處理人物性格,以武犯忌也可以。」
當「武」的展現方式分歧叢生,「俠」的精神又找不到當下的現實錨地與表達空間時,江湖的根基便真正動搖了。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鏢人》的出現顯得意味深長——這部脫胎於現代漫畫的作品,本身就攜帶着一種追問:當傳統俠義遭遇當代語境,它能否以新的敘事語法被重新講述?

《鏢人》與武俠未竟的問答
於是,電影《鏢人》的集結,便承載了多重複雜而微妙的意味。
它像一次無奈又必須的「人才攢局」。陣容本身便是一份行業現狀的說明書:李連杰是黃金時代的隱退符號,吳京是成功轉型主旋律的動作巨星,張晉代表中生代實力派,謝霆鋒則是半路出家、以拼命著稱的「闖將」,至於於適、此沙等新生代,則是尚待市場檢驗的「新血」。
這不是巔峯時期的羣英會,而是一次帶着緊迫感的重現與交接。在影片的前期宣傳中,四代武俠人跨越時代的齊聚概念,意圖傳達一種「武俠技藝的代際接力」之感。而對此類型感興趣的觀衆,也可以將《鏢人》理解爲一場武俠美學路線的重申。
當徐克在《射鵰》中繼續探索武俠的魔幻化時,袁和平選擇在《鏢人》中重返新疆大漠實拍。要求「真打、真摔、真騎馬」,讓演員在壯闊戈壁中「揮灑豪情」。這可以看作是袁和平對「硬橋硬馬」美學的一次大規模、復古的實踐,是用傳統的「笨功夫」,對抗當下流行的、無所不能的特效「魔法」。
想要證明真實的汗水、精確到肌肉發力的招式設計,兵器碰撞的金屬聲與拳腳到肉的物理悶響,依然擁有數字像素無法替代的、直擊臟腑的震撼,正如袁和平早年對3D電影拍攝的要求:「一拳打過去,觀衆要能覺得‘啊’一下,好像真的打到自己身上。」

然而,最核心的,這是一個關於「俠義何謂」的當代詰問,也是《鏢人》面臨的最大挑戰。
金庸式家國大義的宏大敘事已顯疲態,而袁和平自己對於武俠精神的解讀,始終落腳於人性:「什麼叫武俠?『俠』是種人物的性格、主角的性格。俠義精神有很多方面……歸結起來就是武俠精神。俠義俠義,它一定要講義的,不要做違背良心的事,應該出手我就出手,應該容忍我就容忍下去。」過去他強調,電影不能只靠動作,「我是用戲來推動夫妻之情、朋友之情、父子之愛,把人的感情放進去來推動動作。」
另一位導演徐浩峯,則開闢了一條狹窄而深邃的小徑。在他的《師父》《刀背藏身》中,武俠不再是浪漫傳奇,而是高度寫實甚至有些冷酷的「行業圖景」。武林是講究行規與地盤的利益共同體,俠義關乎的是個人尊嚴、師承責任和在一個崩壞秩序中的艱難堅守。
徐浩峯的武打設計短促、兇狠、近乎實戰,他的作品被評價爲「有新意」,但在當下「非常小衆」,未能擴大影響。這是一種文人化、考據化的武俠,將浪漫飄逸的江湖,拉回到佈滿塵土的現實地面。
而《鏢人》原著漫畫,則提供了一種更具張力的可能:它表面上是一個融合了日本劍戟片孤獨美學與美國西部片法外精神的「漂泊者」故事,主角刀馬以「拿錢辦事」的鏢客形象示人。但隨着故事展開,這個「嘴上談利」的刀客,卻在關鍵時刻一次次選擇站在道義一邊——斬殺暴虐的常貴人,押上自己的性命保護知世郎,殺回莫家集救阿育婭。
他的選擇背後,不是簡單的「僱傭契約」,而是一種深植於血脈的俠義本能。《鏢人》並未停留在個人恩仇的層面,隨着護鏢之路的延伸,刀馬的命運逐漸與更大的歷史敘事交織——知世郎「花滿天下」的理想,隋末亂世中黎民百姓的命運,都成爲這趟護鏢之路無法剝離的背景。
它提供的「第三種可能」,或許正在於此:在一個宏大敘事普遍遭遇疏離的時代,能否從一個人「守護眼前人」的具體選擇開始,讓俠義精神自然地生長出家國大義的維度?它抵達的不是反傳統的「現代遊俠」,而是讓傳統俠義在當代語境下重新獲得理解的可能。

江湖很大,燈火尚存
《鏢人》上映後,在袁和平「硬橋硬馬」的動作美學中,還是可以看到原著那種「由個人守護到家國擔當」的精神遞進,只是從票房數字來看,觀衆對此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興趣。在熱鬧的閤家歡的春節檔,它顯得非常小衆——更適合那些對武俠、動作片,或者說對江湖尚存懷戀的觀衆。
這也就決定了,《鏢人》是一次對傳統武俠美學的致敬與回望,也是一次讓俠義精神在當代語境下重新「活過來」的嘗試,並非「重振江湖雄風」的加冕,而是充滿着關於武俠如何續脈的探索意味。
江湖的實體,那個特定的電影產業模式、師徒班底倫理與集體創作氛圍,確然漸行漸遠。當袁和平、徐克等最後一批「舊江湖」的親歷者白髮蒼蒼,一個時代或許真的即將合上帷幕。
然而,江湖的精神,對超凡身體技藝的崇拜,對超越性正義的渴望,對「有所必爲」的浪漫想象,或許並不會消逝。只是需要新的容器,新的語法。正如徐浩峯所言,武打片要復興,必須「接地氣」,「要在武打片裏提供生活的參照」。
我們看到,在主流院線之外,「江湖」正以更靈活、更生猛的形態悄然續命。魏君子作爲製片人的作品《目中無人》系列,在流媒體平臺上以B級片成本,打造了一個「拿錢辦事」卻底線分明的「盲俠」,用凌厲如風的動作和簡潔明瞭的敘事,在年輕觀衆中喚起了久違的快意恩仇。這或許正是徐克曾對魏君子說的那樣:「低成本是你們最大的武器。」
技術的浪潮也在試圖打撈與重塑傳統。諸如一批經典功夫片AI重製項目,試圖用人工智能修復老片,甚至從李小龍、成龍等人的招式數據中,算法生成新的動作美學。中國電影基金會的胡敏闡釋其理念:功夫電影的本質是「用肢體書寫哲學」,以身體實踐重構文化認同,新技術得以讓俠義精神在數字時代生生不息。
這雖是一條前衛路徑,但其成敗,依然取決於能否爲「肢體哲學」找到打動今人的「靈魂敘事」。因此,袁和平與《鏢人》這次集結,其終極意義或許不在於「復興」一箇舊類型,而在於完成一次「盤存」與「交接」。
大漠風沙終會掩埋所有臨時搭建的棧道與足跡,但只要關於公平、信諾與勇毅的內心之火未熄,那麼81歲的袁和平,最終站在了熱鬧喧囂、競爭激烈的春節檔裏,也可以意味着,江湖不會真正成爲絕響,只是需要新的「說書人」,在新的曠野上點燃新的篝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