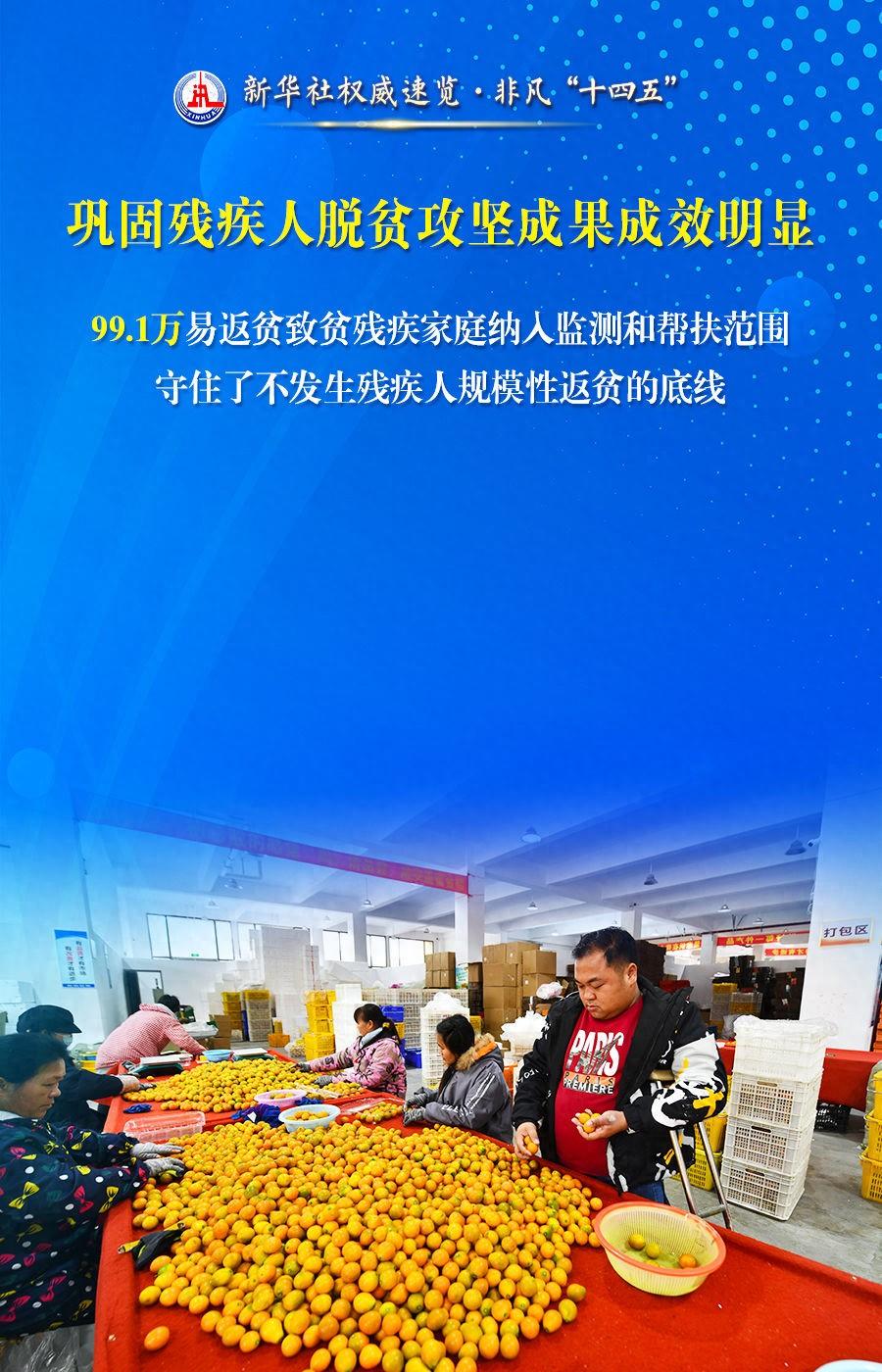蘇超進度過半,南通、鹽城和南京奪得積分榜前三。南通與南京要爲“南哥”一戰,輸得沒有筆畫的“常州隊”墊底,從吊州隊、巾州隊、|州隊變成了0州隊。
“散裝江蘇”聲名在外,喊的口號是“比賽第一,友誼第十四”,“十三太保”各自爲戰,互不相讓的勁頭遠超對外省對手。
這片土地的複雜性遠不止此。“散裝江蘇”的“分裂”感體現在經濟、文化甚至方言的差異上,比如江蘇有至少六種文化圈交織,在方言上還分爲蘇南的吳語區和蘇北的硬核方言區,僅南通一個地級市的方言就高達10種……
但有趣的是,他們都曾鉚足勁兒爲同一件事拼過命——造車,只是如今結局大相徑庭。
在新能源戰場,如果按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爲“江蘇十三太保”排名,當下“蘇超”榜上的“風光”恐要全盤逆轉。根據江蘇省工信部門披露的最新數據,今年上半年,常州、南京、鹽城、鎮江、蘇州五市新能源汽車產量佔全省新能源汽車產量93.7%,“球霸”南通卻不在此列。具體來看:
●墊底的常州已經領跑江蘇,2024年其新能源汽車產量近80萬輛,一人挑起江蘇省65%的新能源汽車產量。
●緊接着便是目前拿下第2名與第3名的鹽城和南京,還在合資與新能源轉型中“掙扎”。
●球榜第一名的南通,卻在造車上落寞,它入局造車最早,交的學費更多。

南通VS南京:球場爭鋒,造車落寞
蘇超積分榜上,南通與南京正爲“南哥”之名角力,但在江蘇造車的敘事裏,兩位“南哥”實則在造車教訓上有的一拼。
視線北移——隸屬南通的縣級市如皋,這裏沒有頂級聯賽球隊,卻在新能源汽車領域押下重注。如皋在新能源汽車產投界以“激進招商”的作風而小有名氣,爲了造車,如皋交的學費不可謂不多。
如皋是最早一批“下海”投身新能源造車的城市,也同時幾乎經歷最多造車“騙局”:從“技術脫節”的陸地方舟和“騙補反噬”的康迪汽車,再到青年汽車的“水氫騙局”和“騙補套利”的賽麟汽車,如皋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界投資上似乎沒那麼幸運。
2009年,國家剛提發展新能源戰略時,如皋就已經開始投資新能源造車產業,成立了如皋新能源汽車產業園區。2010年,如皋就迎來了當地第一家新能源汽車整車生產企業陸地方舟的落戶,這比“蔚小理”的成立早了4至5年。
2013年起,康迪電動汽車、青年汽車、英田、皋開、賽麟開始相繼落戶如皋。根據如皋官方披露的數據,到2017年,如皋新能源汽車產能已經達到26萬輛,產值超過300億元,完成應稅銷售220億元。
然而,如皋在汽車產業上展現了敏銳的前瞻視野,能搶佔早期風口,但投資的目光卻欠缺火候。
青年、賽麟們的騙局讓如皋“一戰成名”。
2016年青年汽車在如皋創辦了青年亞曼,生產氫燃料物流車。當時他們聲稱研發出“水氫發動機”,號稱“加水就能跑”;同一年,賽麟汽車董事長王曉麟用50萬美元買下了美國賽麟汽車品牌的知識產權使用權,然後將其包裝成價值66億元的技術資產,通過“技術入股”的方式與如皋地方政府合作成立了江蘇賽麟汽車,但賽麟只賣出了31輛“老頭樂”;2016年,康迪電動車也捲入騙補案……
沃土爲何結不出好果,卻反噬瞭如皋?正如如皋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陳建軍曾經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總結的經驗:“(地方政府)不能一窩蜂全部上新能源汽車項目,對一些公司的資質,要進行更嚴格的審覈。”
另一位“南哥”——南京的造車之旅也同樣曲折。
南京汽車集團打包“賣身”上汽後,南京又接連在博郡汽車和拜騰汽車上栽了跟頭,如今只剩下上汽系和長安系的工廠還在支撐着南京的汽車產能。
南京是老牌造車城市,1985年,南京汽車集團的成績讓南京在中國自主造車史上留下名字。南汽當時引進了意大利依維柯公司的輕型商用車技術,將躍進車型從NJ130向新產品過渡,在打造輕卡的路上越走越深。
二十多年後的新世紀初,中國汽車產業格局生變,南汽也迎來了一個足以改變自身命運的轉折點——在2005年收購了破產的英國MG羅孚汽車公司核心資產,並由此誕生了名爵(MG)品牌。
後來爲了終結榮威(上汽)與名爵(南汽)兩大同源英倫品牌的內耗,2007年12月,在國家發展改革委推動下,上汽集團以20.95億元現金收購了南汽集團100%股權。
南京也曾在新能源造車熱中走在前列。2016年開始,包括知豆、前途、博郡、拜騰、銀隆、敏安在內的最早一批造車新勢力都入駐南京。
很快,汽車業“擠泡沫”的過程來了,這是政策紅利退潮後,熱錢催生的低技術產能必然需要經歷的一個出清階段。
補貼政策的變動加速淘汰了第一批造車的新勢力,知豆汽車則是其中的一員。它成立於2006年,在2017年達到年銷量4.3萬輛的巔峯,在2018年補貼政策調整後,因續航里程短且技術不達標失去補貼優勢,銷量下滑,最終導致破產。
2020年開始,淘汰賽已經開始加速。博郡、拜騰們倒臺後,更讓南京頭疼的是,南京已經沒有拿得出手的本土新能源品牌。
目前,南京、南通尚未披露最新的新能源銷量數據。而僅有的官方數據還停留在2023年,南京新能源汽車產量僅20.1萬輛,僅爲同期合肥產量的三成不到,距離常州的同期產量差距達到48萬輛。
對比來看,南京面臨的更多是產業升級的挑戰,引入了一大批車企,卻少有能順利活下來;南通則是縣域招商激進帶來的風險失控。
兩位“南哥”交上的多份造車答卷,雖然踩的坑各有千秋,但都寫了一個教訓:地方政府在產業引進上應“重質不重量”,政策支持應從“輸血”轉向“造血”,更加註重企業的技術創新和市場競爭能力。
鹽城:曾是合資優等生,今靠出口撐牌桌
本屆“蘇超”拿到悅達起亞冠名的鹽城隊,也在造車領域榜上有名。
作爲江蘇最“韓”的城市,鹽城曾貢獻了韓系車在華的高光時刻,但同時也共享韓系車在華新能源轉型困難的命運。
但回看鹽城的整個造車史,鹽城十分擅長抓住時機,緊跟大潮。如果說南京是早期自力更生的造車代表,那麼鹽城便屬於合資時代的優秀學生。
鹽城是“悅達起亞”的大本營,悅達起亞是江蘇悅達集團與韓資企業起亞汽車、東風汽車集團在2002年成立的合資車企。當時中國加入WTO後不久,鹽城國資委旗下的悅達集團看準了當時造車的風口,從煤炭企業轉型拓展賣車業務。
東風悅達起亞成立後,靠低價高配的韓系車喫下了中低端市場。2016年,悅達起亞迎來了自己最好的時代,年銷量65萬輛,位居國內車企銷量榜第9位,主力車型包括K2、賽拉圖、智跑等中低端車型,憑藉高性價比覆蓋二三線城市。
但次年的狀況急轉直下,2017年前後,悅達起亞銷量從2016年峯值65萬輛驟降。
同一年,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進入量產時代,新勢力們的概念車陸續開始量產交付,比如小鵬的首款車G3就在當年10月量產下線,成爲最早交付的新勢力之一。
眼看着新的造車時代來臨,鹽城也開始轉型造新能源車,還趕上了新勢力造車的“末班車”,開始在新能源領域白手起家。2017年,高合的母公司華人運通在江蘇鹽城成立。
高合基本上是鹽城市政府扶起來的品牌,鹽城不僅爲華人運通提供資金,還爲華人運通搞定了造車資質。
高合自誕生起就立志做高端新能源車型。2020年,高合的首款車型HiPhi X以57萬~80萬元售價切入市場,成爲當時最貴國產電動車,主打“電動保時捷”標籤。爲了造豪車,不僅大筆投入砸高端產品設計,還在海外商場的頂級商圈開設體驗中心。
定位與市場需求錯配,加上高合盲目燒錢擴張,又主要靠政府輸血維生,高合的崩塌步步加速。
合資品牌則過得更加艱難。如今東風已經退出三方合資,悅達起亞主要靠出口“活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悅達起亞累計銷量12.4萬輛,同比增長13.2%,其中累計出口6.3萬輛,一半銷量都是由出口貢獻。
鹽城還在嘗試轉型新能源,這回將自己的命運和一汽綁定在了一起。去年5月,一汽的鹽城基地已經投產,主要生產奔騰品牌多款新能源主力車型,肩負起帶領一汽轉型的命運。但留給鹽城的,是另一段極具不確定性的新能源征途。
常州:踢球墊底,造車常贏
與南京、南通相比,常州更像是一個眼光獨到、出手精準的風投機構。
常州入局新能源也已經到了2016年,但模式不同的是,常州市政府選擇自己出資參投新能源車企,而包括上海和合肥在內的其他城市也是在2017年開始才參投車企。
這需要足夠的眼光和定力,畢竟2016年,新能源汽車產業的泡沫已經出現,一邊是跨界造車熱,一邊又是“騙補案”下的淘汰賽加速,沒有人能篤定押中的是活到最後的玩家。
2016年,常州在理想汽車成立初期就給予了大力支持。包括土地、廠房、金融貸款等方面的優惠條件,如提供8億元的可轉換貸款,讓理想以低成本拿到理想汽車一期750畝土地。
到2019年,常州又綁定了比亞迪。2019年是比亞迪的低谷期,銷量規模遠不如今。從2017年到2019年,比亞迪連續三年利潤大幅下滑,尤其是到2019年,淨利潤只有16億元。
而今年,理想的下一塊高地——純電的生產也綁定着常州。今年2月,理想汽車宣佈,純電整車工廠將落地常州。第一款純電SUV理想i8將於常州工廠正式量產。
回過頭來看,常州的成功不只在眼光,還有配套的汽車產業鏈集聚爲整車廠的落地託底。
造車之外,常州入局的起點是動力電池,2015年到2016年前後,常州投資引進寧德時代、中創新航等動力電池企業,靠動力電池打下基礎。
蓋世汽車研究院發佈的一則數據顯示,常州的動力電池產業已經形成了全產業鏈深度佈局,擁有電池材料、電池系統技術研發等31個關鍵環節,產業鏈完整度達97%。
目前,常州採用的是整車和動力電池兩條腿走路的策略。整車企業的成功和供應鏈的發展雙向賦能。比如在理想汽車的144家一級供應商中,常州本地就有32家,理想汽車董事長兼CEO李想也曾公開表示,目前理想L系列近地化水平接近60%,預計2026年將達70%。
對常州來說,失之東隅,也意味着收之桑榆。在球場上已經輸到“沒有筆畫”,但在造車這件事,“風投”常州卻直奔江蘇一哥的地位。2024年,常州市的新能源產業規模突破8500億元,整車產量接近80萬輛,佔同期江蘇省新能源汽車產量的65%。
江蘇的造車大業遠不止此,球榜上中游梯隊的蘇州,其下轄的常熟也曾投資觀致汽車、還擁有捷豹路虎的生產基地;位於球榜倒數第二的鎮江也擁有北汽藍谷的工廠。根據21世紀經濟報道的不完全統計,江蘇省13個地級市中,至少曾有20個主機廠在這裏設廠造車。
這背後都得益於江蘇汽車產業鏈的完善佈局。以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爲例,從上游的動力電池以及汽車零部件到下游的充電企業,江蘇省內已形成“材料—零部件—整車—充換電”全鏈條佈局。
然而,汽車產業作爲江蘇製造業的重要支柱,其發展水平直接關係到全省經濟的競爭力。2024年,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第一城”桂冠仍由廣東深圳摘得,且新能源汽車產量爲293.53萬輛,甚至是同期江蘇省新能源汽車產量的兩倍有餘。江蘇汽車產業,尤其是新能源汽車領域,如何發力追趕?從共享經驗到協同,“散裝”江蘇的“十三太保”們也許才能跑出來。
更多內容請下載21財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