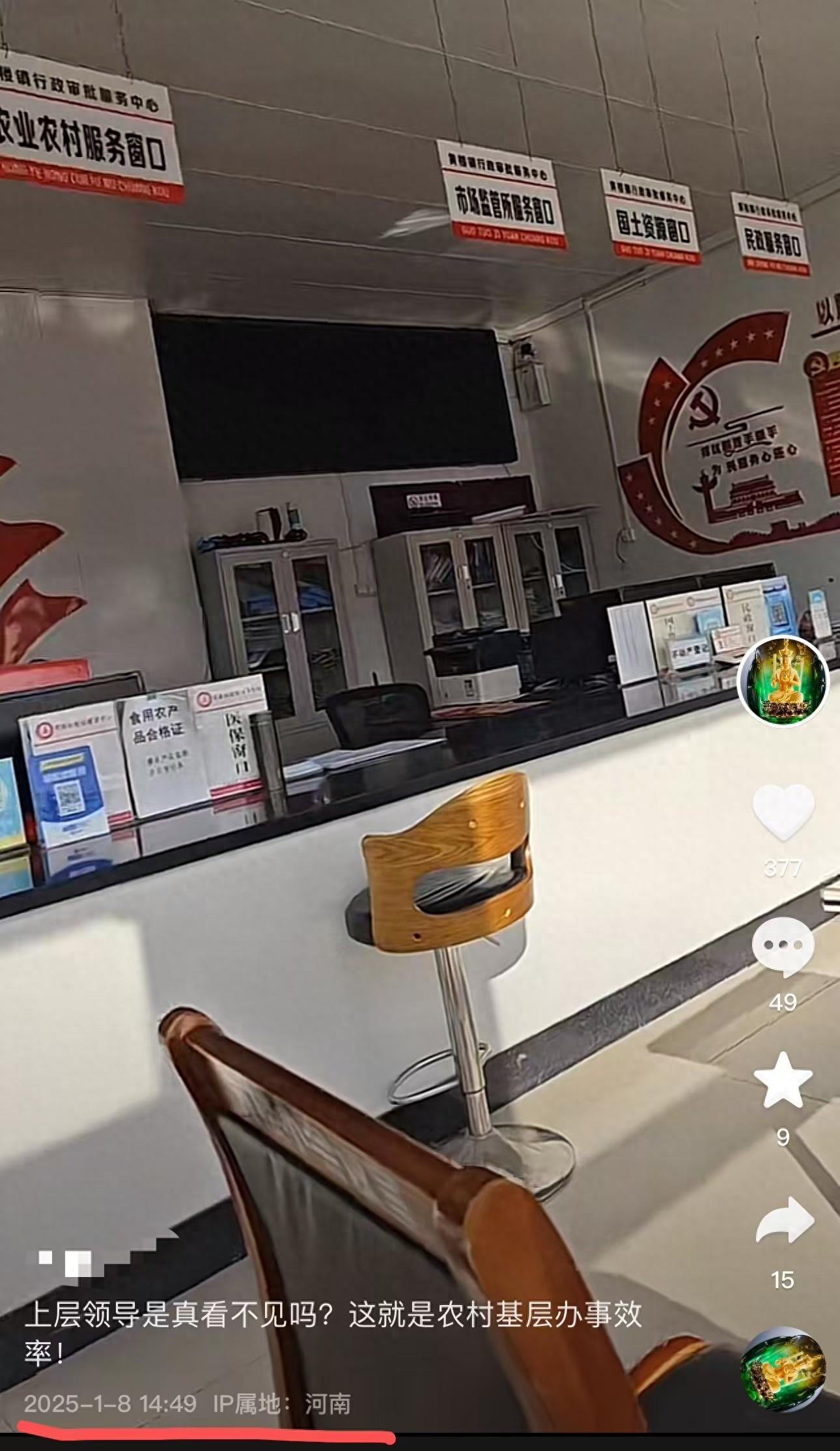1月8日,泰國媒體報道,據泰國皇家警察透露,從初步調查來看,中國演員王星是人口販賣的受害者。當王星和親人準備好後,將與中國大使館協調,預計1至2天可返回中國。
近日,王星在泰緬邊境失聯,王星女友嘉嘉在社交平臺發文尋人,引起廣泛關注。泰國媒體報道,1月7日,泰國總理佩通坦在曼谷總理府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已經確定找到失聯的中國演員王星(星星)。
根據王星描述,他前往泰國是以該國爲中轉點前往第三國參加拍攝工作,卻最終被騙入緬甸。進入緬甸後,王星被迫接受了2到3天的詐騙培訓。王星說,培訓內容以文字詐騙爲主,尚未涉及語音呼叫類或電話對話等詐騙培訓。對此他感到十分恐懼,害怕如果無法得救,自己將被迫以詐騙中國同胞爲生。
近幾年來,緬北涉我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多發高發,早已引發國家層面的關注。2023年7月,公安部部署開展打擊緬北涉我犯罪專項工作。據通報,截至2024年12月底,中緬雙方通過警務執法合作和一系列打擊行動,已累計抓獲5.3萬餘名中國籍涉詐犯罪嫌疑人,臨近我國邊境的緬北地區規模化電詐園區全部被剷除,臭名昭著的緬北果敢“四大家族”之一的明家犯罪集團徹底覆滅。
《中國新聞週刊》曾在2023年對發生在中緬邊境的跨境電信詐騙犯罪進行報道,當時,人口販賣已經成爲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重要特徵。2023年6月7日,國際刑警組織曾公佈了一份關於人口販賣的研究報告,並向195個成員國發出橙色通報,提醒各國警惕由電信詐騙引起的人口販賣。國際刑警組織時任祕書長尤爾根·斯托克說,最初的區域性威脅,已經演變爲全球性的人口販賣危機。
以下是《中國新聞週刊》曾在2023年6月26日總第1097期發佈的文章:
緬北:一場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正在發生
這一晚,陳童又做了同樣的噩夢。她在深山裏迷了路,山的另一邊就是緬甸,她不知道怎樣才能翻到山的另一邊,把弟弟陳晨救回來。
她從夢中驚醒,一身的汗,眼淚不受控制地流下來。
前不久,已經消失十餘天的陳晨突然聯繫上妻子和兩個姐姐,說自己被老鄉騙到緬甸北部做電信詐騙。工作量一旦達不到公司的要求,就會被打。陳晨偷偷發回了自己被鞭子抽打、被錘子砸手的照片,照片中偶爾還會出現其他年輕人,身上是開水燙出的傷口。陳晨向家人求救,希望姐姐早點把自己救出來,“姐求你了”“看看能不能快點”“沒有一天沒有捱打”“我不知道能堅持多久”。
爲了救弟弟,姐姐陳童和陳欣陸續進入了數個討論如何救援被困緬甸家人的羣聊,幾個羣加起來有數百人,大家在找兒子、女兒、弟弟、妹妹、侄子、侄女。一頓飯的工夫,羣裏的未讀消息就破千。“人口販賣”,是羣裏討論的高頻詞。
人口販賣已經成爲跨境電信詐騙犯罪的重要特徵。6月7日,國際刑警組織公佈了一份關於人口販賣的研究報告,並向195個成員國發出橙色通報,提醒各國警惕由電信詐騙引起的人口販賣。國際刑警組織祕書長尤爾根·斯托克說,最初的區域性威脅,已經演變爲全球性的人口販賣危機。

到緬北去
3月22日,被困緬北電信詐騙園區一星期的陳晨鼓起勇氣,偷偷用公司發的手機聯繫上了家人。他不知道自己身處哪裏,以爲是在柬埔寨。陳欣提醒他下載一個地圖軟件,給自己發定位。點開後,雙方纔知道,陳晨在緬甸北部,他們都蒙了。
陳晨原本在一座南方城市送外賣。年初,一位從小認識的老鄉聯繫上陳晨和他的朋友,說有份在東南亞賭場當服務員的工作,一個月能掙3萬元。陳晨的孩子剛上小學,另一位朋友也有不小的經濟壓力。出於對同鄉的信任,他們在3月初啓程了。
老鄉從頭到尾都沒有露面,但爲陳晨安排好了所有行程,讓他們先坐車去貴陽,然後再乘飛機。到了貴陽,行程卻變了,有一輛私家車專程來接他們。路上,又有一個人加入了他們,是老鄉的表哥,他也是奔着傳說中的高薪工作去的。
私家車一路向西南開,通過辨識路牌,陳晨發現已經到了雲南的德宏芒市。沿山路開了40分鐘,陳晨漸漸感到不對勁了,手機定位顯示已經靠近緬甸邊境。隨後車突然停住,一下車,陳晨三人的手機就被收走,又被送上另一輛車。
經過幾趟換乘,陳晨三人被送到一座山上,一前一後兩人押着他們爬山。陳晨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兩人都是1.7米多的身高,身板很壯,皮膚黝黑,口音不像中國人,都帶着刀。爬了四五個小時的山,到達中緬邊境時,已是晚上11點。過了一會兒,押送的人讓陳晨三人走過一道鐵門,穿過門,他們便被送到了電詐園區。
聯繫上姐姐後,陳晨把被騙的經過和自己在公司的遭遇零零散散地告訴了她們。每次陳童或陳欣都要先和弟弟對暗號,確保他周圍無人監視才方便溝通。聊完後,陳晨會馬上把對話刪除。
陳童和陳欣每天在羣裏和受騙人家屬交流,發現困在緬甸電詐園區的人都有着相似的遭遇。
19歲的吳洋和朋友四處找尋工作機會。交友軟件上相識一週的女生告訴他,自家親戚在緬北經營KTV,招募酒水銷售,只需每晚工作幾小時,就可以拿到8000元底薪和額外的提成,另外,還能幫他們解決路費和當地住宿。
可以出去見世面,又可以賺錢,吳洋和朋友都心動了。第二天,他們就啓程了。對方幫他們買了前往雲南省保山市的機票,機場外有人接他們,開車帶他們到了邊境。
從這裏開始,一切都不對勁了。吳洋和朋友沒有預料到,對方會不帶他們從正常途徑出境。全國各地來的一二十人,被蛇頭帶着,在中緬邊境的大山裏穿行。天色已晚,山路陡峭,人隨時都可能墜落山崖。
一夜之後,他們到達緬北,並被一輛車接走,送進KTV所在地。大門口有穿着軍裝、揹着槍的人把守,樓內只有三四間KTV,其他房間門鎖緊閉,吳洋疑竇叢生。接近地下室時,他聽見哀叫隱隱約約傳來。一個只在電影裏見過的水牢赫然出現在眼前,一豆燈火虛虛地亮着,只看得見水和欄杆,看不清裏頭的人影。
吳洋徹底反應過來,這個地方有問題,但走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從事電詐
吳洋和朋友被收走手機,帶進了一個房間。百來平方米的空間裏擺了三張長條桌,二十來人散落在桌邊,彼此用隔板隔開,看起來都在低頭忙着自己的事情。幾名高高壯壯的看守手持電棍,在屋裏巡邏。有的人臉上、身上有新的傷痕,一看就是電棍打的。
看守給吳洋及朋友講解上班規則,他們倆被安排在毫不相鄰的位置,不準互相聯繫、說話。倆人都上夜班,從夜裏12點到中午12點,任務是在聊天羣裏引導用戶到固定的網絡賭博平臺充錢。上班時間以外,他們也不準離開這個房間,只能趴在桌上休息。
吳洋這才意識到,自己正深陷一個電詐集團。很多人被帶到電詐園區後,會被公司要求籤合同。田小北的弟弟也被騙到了緬北電詐園區,他剛到公司就被強迫簽了兩年的合同,裏面規定必須做夠時間或者出單了,纔有可能離開。所有人在公司不用真名,必須使用代號。
業績是每天一睜眼最重要的事。陳晨所在的公司做“殺豬盤”,他剛到就接受了培訓:怎麼和客人打電話,怎麼讓客人對自己產生興趣,怎麼一步步加到客人的微信。然後就是實操,每天有規定的工作量,必須打滿一定數量的電話,加到一定數量的新人的微信。田小北弟弟所在的公司專做歐美“殺豬盤”,主攻社交平臺臉書,大家每天按照公司編制的流程,用翻譯軟件和外國人交流。
吳洋則被髮了四五臺手機,裏面沒有微信、QQ這類人盡皆知的App,以防他們跟外界聯繫。手機裏只有一個他從未見過的社交軟件,看守們說,許多玩網絡賭博的人都用這個App。
幾個不同的手機註冊了App不同的賬號,被拉進相同的聊天羣,吳洋需要用話術打動網絡那端的賭徒,“我今天充了XX元,賺了很多。”另幾個號立即跟上,“我也是,我也賺了。”以此誘使他人充錢。
公司要求的工作時長几乎沒有低於16個小時的。陳晨每天早上8點起牀,會一直工作到凌晨2點甚至4點。而專做歐美“殺豬盤”的公司,要求工作作息和客人保持一致。田小北弟弟的公司晚上10點上班,第二天下午5點下班。
每一兩週,看守們要考覈工作量。吳洋所在的公司規定,如果沒有拉足10名客戶,要接受狼牙棍懲罰。如果不服管教,則接受電棍懲罰。打多少沒有規定,自然是打到看守們覺得可以了爲止。
吳洋因爲任務不達標,被狼牙棍打過,棍子上一根根的刺刺進肉裏,很長一段時間內,吳洋的後背都佈滿密密麻麻的小疙瘩。他的朋友從進屋子起,就鬧過幾次,極不願意做這些事。看守們一開始拿狼牙棍打他,後來直接動了電棍。
陳晨剛到公司,就被來了個下馬威,打了30多鞭。陳晨記得,同公司有人無法完成業績,被吊起三四天,期間不能喫飯和睡覺。有人被關進狗籠,四肢在籠裏無法伸展。有人筋骨硬,就被幾個人強按着劈叉,同時嘴裏被灌着水,不讓喊出聲音。
沒有完成工作量的人,一天往往只能喫一頓飯,當然飯也是自費的。吳洋在第一個月結束的時候,拿到了3000元工資。錢自然是留不住的,這裏伙食差,每天基本都是白菜、米飯,一週最多能見一次葷腥。他拿錢打點看守,請他們幫忙買喫的,對方的報價是國內的兩三倍。
田小北的弟弟和家裏聯繫上之後,家裏給他轉過幾次錢,因爲弟弟沒有業績,喫不起每天40元一頓的工作餐。還有人用公司發的生活費喫飯,這些錢都被公司一筆筆記到他的賬上,成爲他的債務,之後需要償還給公司。
逃,還是不逃
所有人都想過要逃跑,但逃跑是一個難度重重的選項。
有些園區連找到通往外面的路都很難。田小北的弟弟說,園區裏有大大小小几十個公司,每家公司幾十人到上百人,整個園區有幾千人,在園區裏走一圈要花20分鐘。
更何況,園區把守森嚴。“整個宿舍和工作的地方,都被鐵皮圍起來了,上面有幾圈防盜網,並且四周都有監控。”陳晨回憶,園區裏到處都有荷槍實彈的看守,去喫飯都有二十多人守着。
李冬梅的兒子也被騙至緬北,他練過散打,動了逃跑的念頭。但李冬梅很快收到兒子的信息,說前段時間有兩個人逃跑,好像已經被打死了。同鎮另一個陷在緬北電詐園區的孩子家長告訴李冬梅,自己兒子嘗試過逃跑,被抓了回去,肋骨打斷了一根,後來她和兒子失去了聯絡,不知道兒子是否還活着。
吳洋是其中難得成功的。極度驚恐地過了三個月,吳洋的膽子大了起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聯繫自己一起被騙來電詐公司的朋友。沒有微信和QQ,他就在聊天App的羣裏觀察,誰也有類似的話術,再通過句尾語氣詞、常用語縮小範圍,確定某個人可能會是自己的朋友。
吳洋偷偷單加了他好友,一面害怕萬一加錯人,東窗事發,自己會被狠狠地懲罰,一面又滿懷期待、含含糊糊地問了一句話,你是從海南來的嗎?對方想了很久,終於慎重地打出兩個字,是的。二人從初中就相識,共同的回憶數不勝數。互相說了幾件只有對方會知道的事,自此相認。
話題轉回到最迫切的事上來,要不要逃、怎麼逃。每天的工作時間,他們趁看守巡邏其他區域時,用手機偷偷摸摸聊上幾句,慢慢探討出一個可行的逃跑方案。
大樓的前門有人值守,後門則沒有,且通向外頭的馬路,並無阻攔。他們所在的位置是二層,跳下去不可行,但吳洋記得,最開始在樓內瞎逛的時候,看到過窗邊的水管,似乎可以借力滑向一樓。看守們每天都會在晚飯前外出三五分鐘取外賣,這是他倆唯一能出逃的機會。
逃,意味着自由,可也意味着一旦失敗,他倆將面對更嚴苛的監禁,甚至死亡。二人都很謹慎,反反覆覆商榷。直到某天下定決心,第二天就跑。
傍晚,看守們外出拿飯了,吳洋和朋友對視一眼,相繼跑向正對後門的窗邊。他們的記憶沒有錯,窗外確實有根水管,二人抓住水管,滑向一樓。大半年來,雖然和房間裏的二十多人朝夕相對,但彼此不通姓名、不知底細。大家都看見了他們的行爲,但最終沒有人跟着一起逃。
之後的一切都有驚無險。看守們反應過來時,二人已經跑了很遠。他們特意跑向人多的地方,又在巷子裏七彎八拐地穿梭,甩掉了追來的人。他們買了路邊攤最便宜的手機,向家人報了平安,並攔了輛出租車,直奔中國國門。
到達中國國門時,距離二人出逃,纔過去短短一個小時。

真實的緬北
短視頻平臺上曾廣泛流傳一段視頻,低沉的男聲說,“這裏是緬甸北部,我生長的地方。歡迎來到我的世界,嬌貴的小公主。”緬北被描繪成一個紙醉金迷、歲月靜好的掘金地。而實際上,緬北並非如此。
張焱是南方某地公安局駐雲南的民警,從2021年中開始負責滯留緬甸人員的勸返工作。據他的初步估計,僅僅是緬甸東部的妙瓦底就有上百個園區,緬甸的勐能、勐平、邦康、大其力、南鄧、老街、木姐等地加起來至少有1000個園區,“差不多有數十萬人在那邊敲鍵盤”。
廣東警官學院副教授莊華和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馬忠紅在發表於2021年的《東南亞地區中國公民跨境網絡犯罪及治理研究》中指出,據統計,從緬甸抓獲的網絡詐騙人數應該位列東南亞各國之首,其中緬北地區在跨境網絡犯罪窩點地中具有“大本營”地位。
緬北地區之所以集中出現大量電詐園區,存在歷史原因。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戴永紅指出,緬北主要指緬甸北部的克欽邦和東北部的撣邦,緬邊境雲南段1997千米,除了與德宏州相對的緬方一側爲緬政府控制以外,其餘地州緬方一側均爲緬甸地方民族武裝(以下簡稱民地武)勢力所控制。
1947年,緬族精英與各少數民族首領共同簽訂了《彬龍協議》,建立聯邦制國家,承認民族平等與民族自決原則。但之後,緬甸政府軍和地方武裝力量長期爆發衝突,尤其小規模的戰事衝突已是家常便飯。
如今,民地武勢力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在了緬北地區,但雙方始終處於拉鋸狀態。雲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實踐中心主任簡琨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民地武爲了獲取鉅額軍費,選擇了走私、毒品交易、賭博、人口買賣等犯罪作爲財源。這也導致緬北地區出現了世界罕見的局面,以準國家的形式支持犯罪。
電詐團伙原本的聚集地並不在緬北,有不少是從國內出境的。因國內打擊力度日益加大,電詐團伙轉而出境尋找落腳點,但詐騙對象始終是中國人。他們輾轉過歐美、日韓、非洲、柬埔寨等地,逐漸從對詐騙有嚴厲的司法打擊、執法能力高的地區,遷徙到對詐騙的刑罰措施低、執法能力弱的地區。隨着我國與各國簽訂國際刑事司法合作條約,電詐團伙紛紛前往司法真空地帶緬北落腳。
簡琨益說,刑事司法合作,有國家之間的,也有地區之間的。但如果要和緬北的民地武進行此類合作,則涉及一個重要外交議題,即如何定義民地武。據他所知,無論是我國國家層面還是邊境省級層面,與民地武均沒有簽訂此類合作條約。
除此之外,還有多重原因使得中國的電詐團伙在此聚集。簡琨益在中緬邊境走訪時也發現,邊民的國別概念較弱,管理始終是一大難題。尤其是一寨兩國的地方,村寨一半在中國,一半在緬甸。村民說雲南話、用人民幣,手機信號是移動聯通,手機支付用支付寶、微信,孩子上學、家人看病都要跨境來中國,很可能一家人裏,哥哥姐姐住在緬甸,弟弟妹妹住在中國。
在文化背景相似、來往頻繁的前提之下,電詐集團與緬北民地武更容易一拍即合,且便於偷渡。簡琨益指出,他們彼此語言相通、文化相通、認識相通,“前者想找保護傘,後者想要客戶,權力與犯罪很容易建立關聯。”
緬北的人羣也因此形成了魚龍混雜的局面。有當地人,有與之來往密切的雲南邊民,也有被吸引前往的犯罪首領、中層以及馬仔。

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
在此背景下,犯罪組織通過偷渡向緬甸電詐園區輸送人力的產業鏈逐漸形成。
許昌市公安局警察杜廣雷和中國人民警察大學講師張婷與100餘名偷越國境的違法犯罪人員進行了交流,又對三十多個犯罪團伙和典型案件中的1000名涉案人員進行了綜合分析,並於2022年將成果發表於一篇論文中。他們發現,多數偷渡者淪爲犯罪組織賺錢的工具,犯罪組織以3萬~15萬元不等的價格,將偷渡者分流至賭場或詐騙組織。陳晨進入電詐園區後才知道,當時把自己騙上路的老鄉能夠從中得到抽成,算上陳晨、陳晨朋友和老鄉的表哥,進賬至少幾萬元。
除了從國內將偷渡者賣到緬甸各個電詐園區,緬甸不同電詐園區之間也存在人口販賣行爲。
一次聯繫中,李冬梅的兒子說自己因爲沒有業績,被公司威脅,“再不出業績就賣到其他園區”。李冬梅着急了,害怕兒子被賣到其他園區之後,又聯繫不上。這種情形在尋人的家長羣裏太常見了,有些家長的孩子已經被轉賣過幾次,越往後業績壓力越大,因爲越往後販賣的價格越高,這筆賬都被公司算到個人身上。
有些電詐公司的人口販賣已經出現明顯的綁架特徵。一位江西父親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兒子在過年前被騙到緬北電詐園區,由於一直出不了業績,被視爲累贅。兩個多月後,公司讓兒子聯繫自己,出錢把人買回去。
國際刑警組織於6月7日發佈的有關人口販賣的研究指出,數以萬計的人正在東南亞被販賣,這種人口販賣現象最初出現在柬埔寨,後來又延伸至老撾和緬甸,如今還有至少4個亞洲國家出現了販賣中心。
國際刑警組織在研究中還指出,之所以會出現規模如此龐大的人口販賣現象,是因犯罪組織利用了後疫情時代的特點——越來越多事務只能在線上處理,使得電信詐騙的數量急劇增加,與此同時,許多人失去了工作,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工作機會,因此更容易被高薪工作所誘騙,成爲電信詐騙的工具。
在簡琨益看來,近些年來,隨着緬北地區犯罪組織的壯大、網絡化,實際上這些組織已經呈現出跨國有組織犯罪的趨勢,而犯罪集團一旦呈現有組織化,人就具有了雙重價值——第一是作爲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對象,第二是作爲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工具。
當人作爲犯罪對象,犯罪組織唯有通過誘騙、綁架被害人才能勒索大量的贖金,實現物質利益的目的。當人作爲犯罪工具,犯罪組織會通過轉變被害人成犯罪人的方法,來不斷壯大組織。簡琨益說,從實際案例來看,被打掉的犯罪組織,其中的成員有很大一部分一開始是被騙到緬北的被害人,此後轉變成爲犯罪組織的成員。
“國際刑警組織提出的‘全球性人口販賣危機’應當進行一種現代意義的解讀,這不同於傳統的拐賣人口並從中獲益,而是跨國有組織犯罪以壓榨人權獲得利益的一種內循環:要不將人作爲人質獲得利益,要不將人變成組織成員獲得利益。”簡琨益說。
(爲保護隱私,文中陳童、陳晨、陳欣、吳洋、田小北、李冬梅、張焱爲化名)
編輯:陳婉允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