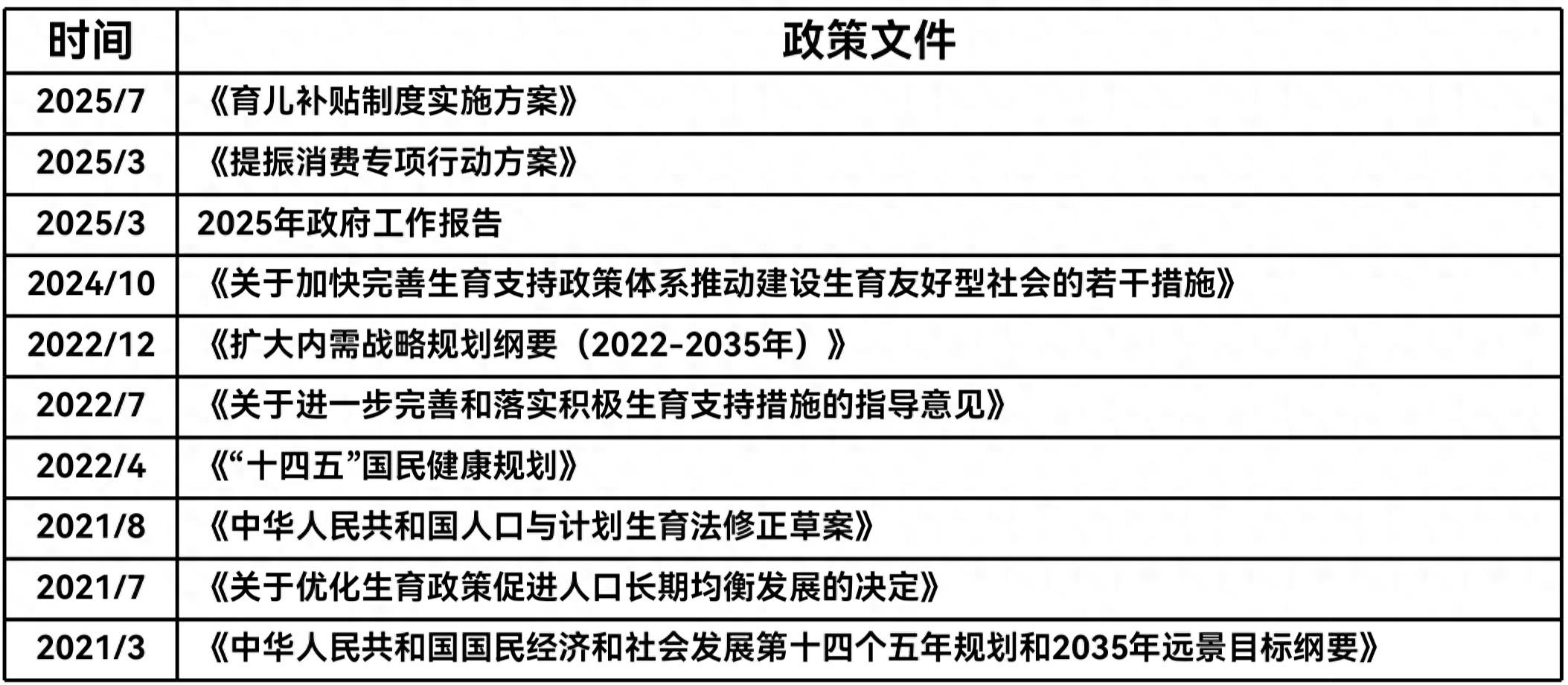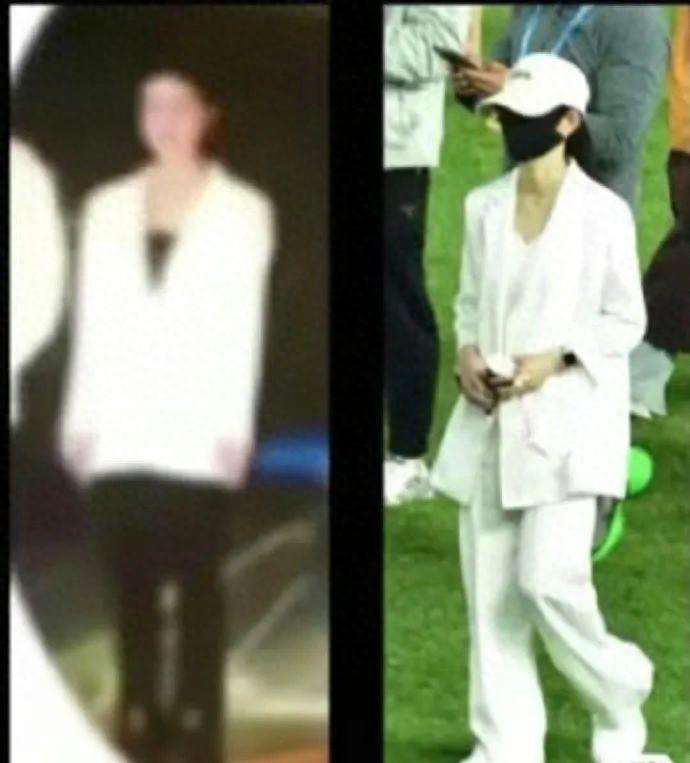本文爲深度編譯,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日新說觀點

關於以色列在加沙地帶軍事行動的性質,一場激烈的辯論正在全球範圍內展開:其行爲是否足以被稱爲“種族滅絕”?持不同觀點的人們,無論是認爲其符合“種族滅絕”定義者,還是堅稱此說法過於誇大者,都共同希望自己的論點能影響更廣泛的公衆認知。然而,這場討論本身正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問題——它在震驚與麻木之間,模糊了焦點,甚至可能適得其反。
“種族滅絕”這個詞,如今無處不在,縈繞在人們的屏幕和夢境中,其煽動情緒的程度堪比任何其他術語。它具有多重意義,包括法律、道德、歷史、比較和戰略層面:它是否符合聯合國1948年制定並納入1998年《羅馬規約》(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律基礎)的法律定義?出於道德考量,是否應該使用這一術語?它是否與過去或現在的種族滅絕行爲具有可識別性?
然而,無論使用還是反對這一術語的人,似乎都認同一個共同因素:其戰略潛力——他們希望這一論點能改變人們的觀念。但這真的有效嗎?

以色列活動人士週二在特拉維夫示威,反對加沙戰爭。
震驚與麻木:一場混亂且廣泛的辯論
目前很難判斷這場辯論的效果,因爲它已經變得混亂且非常廣泛。全球頂尖的種族滅絕研究專家之一奧默·巴托夫,最初在長篇且充滿痛苦的論文中認爲,2023年11月對10月7日事件的戰爭尚未提供種族滅絕的證據,但現在他認爲證據已經存在。
他的主張引發了廣泛回應,從學術博客對這場辯論所代表含義的審慎探討,到《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佈雷特·斯蒂芬斯的回應。《國土報》也就該問題展開了激烈辯論,巴托夫與包括頂尖思想家和學者在內的其他聲音相互辯論並回應。
此外,許多使用該術語的團體或發言人沿着部落或意識形態光譜分佈:那些在10月8日就指控以色列犯下種族滅絕罪的人,很可能在10月7日之前就認爲以色列正在這樣做。這些並非善意論點。
另一些團體,如大赦國際,在戰爭開始後等待了一年多,於2024年12月發佈了一份近300頁的詳盡研究報告,該報告基於超過200次採訪。但這份報告的結論從一開始就毫無懸念。
此前已在去年12月發佈了一份七頁摘要,並承諾將發佈一份單獨的報告探討該話題。大赦國際的種族滅絕報告引發了與該組織以色列分會的衝突,後者質疑該結論。大赦國際隨後暫停了以色列分會兩年。

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城今日早些時候聚集,從慈善廚房領取食物,以應對饑荒危機。
而在辯論的另一端,巴伊蘭大學的丹尼·奧爾巴赫、喬納森·博克斯曼、亞吉爾·亨金和喬納森·布拉弗曼近期發佈了一份長達277頁的報告。該報告系統、比較且定量,同樣基於廣泛且透明的來源。然而,結論同樣毫無懸念:大多數章節指出,幾乎所有來源——包括國際人道主義機構、戰爭學者、醫療專業人員及全球媒體——關於加沙毀滅性破壞的指控,要麼是錯誤的、誇大的、被誤解的,要麼與其他戰爭相比相對正常。

去年在賈巴利亞難民營執行任務的以色列士兵。
當然,在另一端,以色列最堅定的支持者否認以色列可能犯下種族滅絕罪,而他們需要的唯一“證據”就是駁斥種族滅絕指控本身。
值得玩味的是,無論是《紐約時報》的佈雷特·斯蒂芬斯,還是巴伊蘭大學報告的作者,都對貶低或淡化“種族滅絕”這一術語表示擔憂。
“與其威懾侵略者並防止暴行,‘種族滅絕’這一術語將失去其深刻的法律和情感分量,淪爲政治工具。在未來危機中,包括那些存在蓄意、系統性消滅民族或羣體行爲的危機,種族滅絕的輕描淡寫將爲未來暴行提供藉口……旨在保護弱勢羣體的國際法可能遭到嚴重削弱,這對全人類都將產生嚴重後果,”巴伊蘭大學報告的作者寫道。

荷蘭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外觀。
這種邏輯令人費解:世界上某個地方的種族滅絕罪犯計劃消滅一個羣體,但他卻擔心自己會被指控犯有種族滅絕罪。然後他想起這個詞已經被貶低,可以適用於任何極端戰爭情況。於是他滿意地繼續肆意犯下暴行,而這種情況在全人類中重複上演?或許這種邏輯本身就存在誤解。
或者,雙方的論點只是引發情感反彈,導致人們固守既有信念。在這種情況下,這場辯論的意義究竟何在?
在混亂中尋找意義:誰在爲何而戰?
既然意圖在關於種族滅絕的討論中至關重要,我們有必要回顧各方在試圖做什麼:那些以嚴肅態度研究和撰寫種族滅絕問題的人,正竭力阻止它發生。那些花費時間和精力在加沙的浩瀚慘劇中篩選細節、拆解種族滅絕嫌疑的人,又在竭力……做什麼?
人們無法擺脫這樣的印象:那些投入巨大努力來駁斥種族滅絕指控的人,最終目的是爲一場在當前情況下顯然無法正當化的戰爭辯護。

《紐約時報》的斯蒂芬斯認爲,應避免使用該術語,因爲它助長了基於惡意指控的反猶太主義刻板印象。這是一個正當的擔憂,但它完全忽視了世界上一些頂尖研究人員(其中許多是猶太以色列人)提出的嚴肅種族滅絕論據,而這些論據的唯一目的是:阻止屠殺。
以下是兩個極具價值、經過深思熟慮的種族滅絕研究案例。歷史學家李·莫爾德恰伊撰寫了一份令人震驚的詳盡報告,記錄了加沙的災難性破壞,報告持續更新,資料詳盡且易於閱讀——這完全出於他個人的良知,而非任何組織或機構的議程。
另一位世界頂尖的種族滅絕研究學者A.迪爾克·莫西斯有力地論證了國際法對種族滅絕的定義本就不充分,因爲這些定義原本旨在狹隘地適用於戰爭中國家對敵方實施的殘暴屠殺。

這一洞見同樣適用於其他衝突,例如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衝突——而這一論點的核心意圖,是重新審視該術語的定義,以阻止針對人類的罪行。
如果“種族滅絕”一詞讓你個人感到不安,那就先放下——轉而關注《國土報》記者尼爾·哈森的持續調查,這些調查回答了諸如爲何如此多加沙人在試圖前往食品中心時被射殺,以及實際死亡人數是多少等問題。看看那些飢餓兒童的照片,別再糾結於如何命名:專注於結束戰爭。
我理解那些覺得被那些不願意使用這個詞的人拋棄的巴勒斯坦人。但現在,語言上的測試不如團結所有支持結束這場戰爭的人重要,無論他們使用什麼語言。雖然我個人可以理解那些被迫整天反駁種族滅絕指控的人的情感痛苦,但問題仍然是:你站在歷史和人性的哪一邊?

遠比這糟糕得多:一場歷史的迴響
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我不禁回想起2017年對種族隔離辯論的分析。當時,正如現在,這個詞本身已成爲爭議焦點。正如我當時在《+972雜誌》上所寫:
“悲劇的現實是,以色列是否與種族隔離制度的政策如出一轍,其實並不重要。……結果是,阿拉伯人與猶太人被系統性地分離,通過教育、機會、土地、道路和水資源,而在西岸,則通過法律。……作爲一名以色列人,我問……我們真的想討論這個問題嗎?我們是否應該在細節上糾纏不休,計算得失,來決定以色列是否在實施種族隔離?佔領本身已經夠糟糕了。讓我們結束它。”
如果將那個時代有毒的言辭替換爲當今有毒的現實,不難看出其中的平行之處。
我們爲何要進行這場討論?如果“種族滅絕”一詞讓你感到不安,那麼真正應該讓你不安的是加沙的現實。
作者:達莉婭·施恩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