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蝸居》播出十七年了,《我的前半生》也過了九年,這樣的時間跨度,足以讓兩部戲從熱播變成舊番,但它們卻意外翻紅了。“我已經到了兩邊都理解的年紀”成爲了這兩部劇的熱門話題。
幾乎每隔一陣,就會刷到《蝸居》中海藻摘耳環那場戲,各種翻拍解讀,土純風三個字硬生生被歸納成了一種美學。《我的前半生》更不用說,劇裏唐晶那句“我也能養得起你”,在每個討論國產劇的角落裏,依舊被反覆提起。


當年看,其實都是別人的故事。
海藻選錯男人,活該。羅子君被離婚,可憐。唐晶那麼強,是女性的榜樣......觀衆如同閱卷老師,評價三觀,指點人生。而這兩部劇也像《甄嬛傳》一樣,從一部作品,慢慢轉變成公共素材庫,當中橋段被拆開、臺詞被重估、角色的動機被再次審視,但我們還是不禁疑問,爲什麼是這兩部劇翻紅?爲什麼是現在?
可能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案是,觀衆逐漸看懂了。

彼時海藻在車裏說的那句“人情債,肉償了”,當年我們只聽到道德淪喪,如今觀衆依舊批判這種不倫關係,但與此同時卻也能體會一個普通女性處於生存焦慮下的無奈。彼時羅子君脫下高跟鞋赤腳踩進積水,當年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婚姻失敗的狼狽女人,如今卻能從其中感受幾分堅韌。

女性面臨的困境從未消失,現在房子依然捆綁着愛情與安全感,獨立女性依然被期待活成某種標準模板,只是多年前我們以爲那只是電視劇主角需要面對的問題,如今才明白,生活給了我們同一套考卷,我們只是晚幾年進場。
所以重溫這些老劇,從來都不是爲了懷舊,是想確認,當年讓我們憤怒的、鄙夷的、困惑的那些選擇,如今再面對,又會怎樣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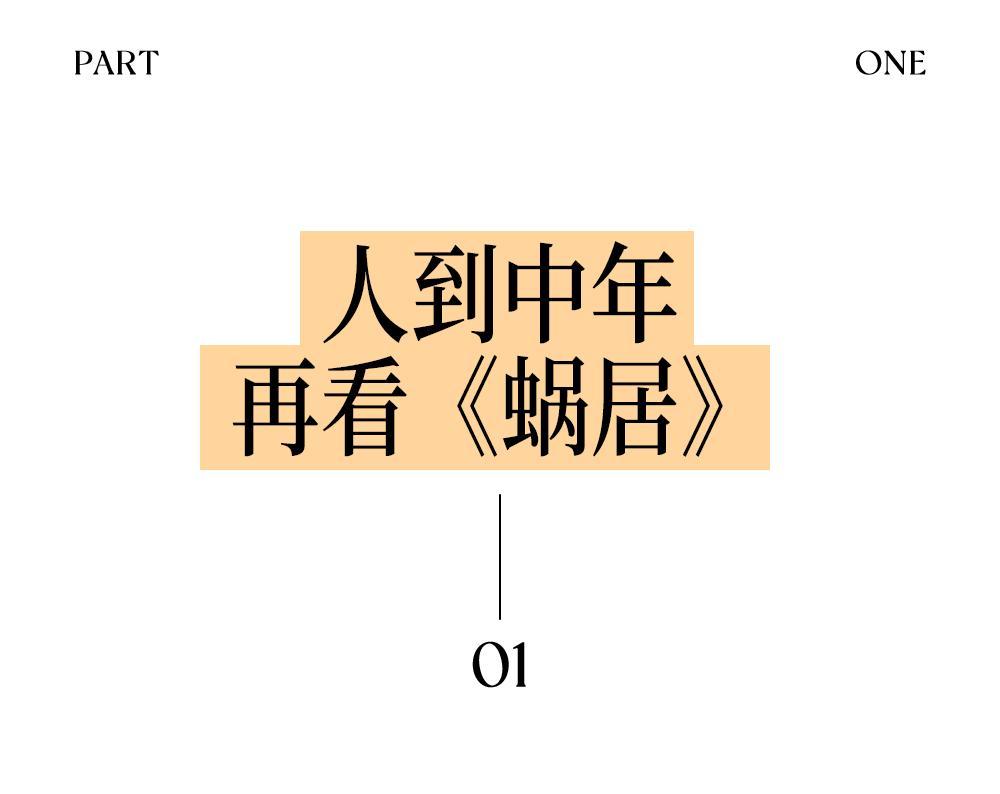
在《蝸居》上映的2009年,其實正處於全球金融危機時期,國內房價開始起飛,這部電視劇則講述了一個普通家庭在一線城市落戶安家的故事。
姐姐海萍與丈夫蘇淳,名校畢業,留在上海。他們的家,是租來的十平米石庫門亭子間,攢首付,是海萍生活的唯一重心。而妹妹海藻和男友小貝,合租在三居室的一間屋裏,計劃着存款數字跳到某個節點就結婚。

一切的改變都是從海萍四處籌首付款開始,初入社會的海藻爲了幫姐姐減輕壓力,最終成了已婚市委祕書宋思明的情人,但海藻面對的選擇從來都不是兩個男人,而是兩種生活。
男友小貝代表着簡單的愛情,純粹但易碎,他買得起哈根達斯但買不起上海的一平米,他給的感情很真誠具體,卻在一個更龐大的遊戲裏,被預設了購買力上限。而宋思明帶來的是金錢、是權力,他能解決麻煩,能跳過普通人需要遵循的規則,像他說的,凡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大問題。

而海藻的墮落,如今也被我們重新檢視,現在看她,會覺得憤怒少了,悲涼多了。觀衆開始注意那些曾被忽略的細節:她的動搖與掙扎,並不是因爲名牌包,而是看着姐姐和丈夫,被困在狹小的弄堂房,每天爲錢爭吵,愛情被消耗殆盡,相互之間只剩埋怨,她也看到了一種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未來。
一個年輕女孩,在那樣原始的生存焦慮面前,手裏能握住的籌碼如此之少,她的身體與情感成了唯一可快速變現的資產,然而這也正是故事殘酷的地方。
海藻並不是那種爲了物質入場便能輕鬆做到只圖物質的人,她對宋思明,在依賴與索取之外,也產生了真實的、混雜着崇拜、感激與某種被庇護安全的依戀,她會在深夜等他回家,會因他的關心而雀躍,會認真地糾結於他是否“真的愛她”,她反覆對海萍說:“我是真的愛他。”

這句話,當年被當作自我洗腦的笑話,如今再聽卻透着一種令人心酸的認真。她的悲劇不在於徹底的物質化,在於她的情感,最終無法自控地寄生在了不倫的關係裏,讓她徹底失去了道義的高地與退路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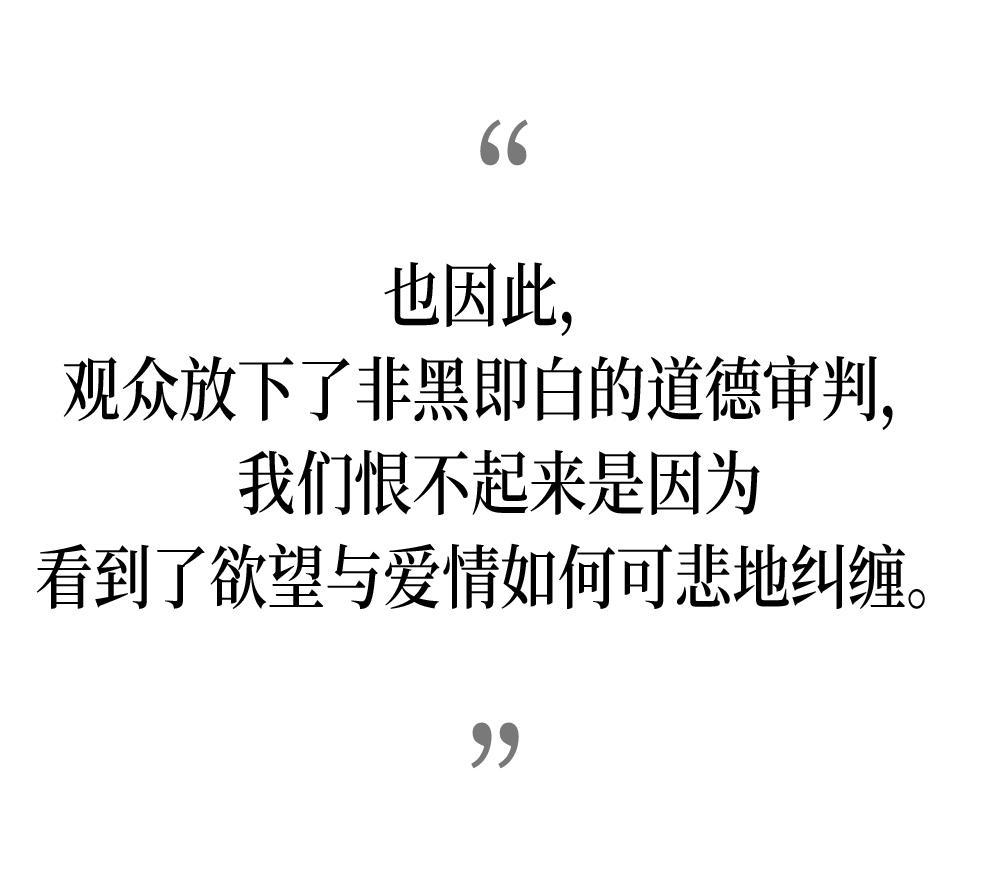
《蝸居》的翻紅,是因爲它提前十七年,預言了直到今天也存在的困境:在一個被物質、權力與生存焦慮高度結構化的世界裏,愛情如何保持它的純粹性?當情感與交易、真心與計算、依賴與獨立早已難分彼此,我們又該如何定義一段關係的性質,如何安放自己那顆必然摻雜了諸多現實考量的心?

而當視野拓寬至同期作品,這條愛情觀的演變脈絡更爲清晰,早兩年的《奮鬥》裏,年輕人的痛苦還圍繞着理想與自我,愛情作點綴。到了《北京愛情故事》,現實已從背景走到前臺,物質開始明目張膽地爲愛情標價、分流甚至審判。《蝸居》正處於這個轉折點上,它赤裸地展示了,當生存的邏輯全面碾壓情感的邏輯時,一個普通人,尤其是一個普通女性的選擇與改變。
不過當下,我們卻逐漸意識到那道選擇題本身,或許就是一個陷阱。


爲什麼一個女性的安全感和未來,似乎總得通過與某個男性的關係來兌換?爲什麼“愛情”與“生存”會被放置在天平的兩端,且重量從未對等?海藻與宋思明的故事,沒有給出答案,只是將這道無解的難題,連同全部的灰色地帶,直白地、不加掩飾地,重新又攤開在觀衆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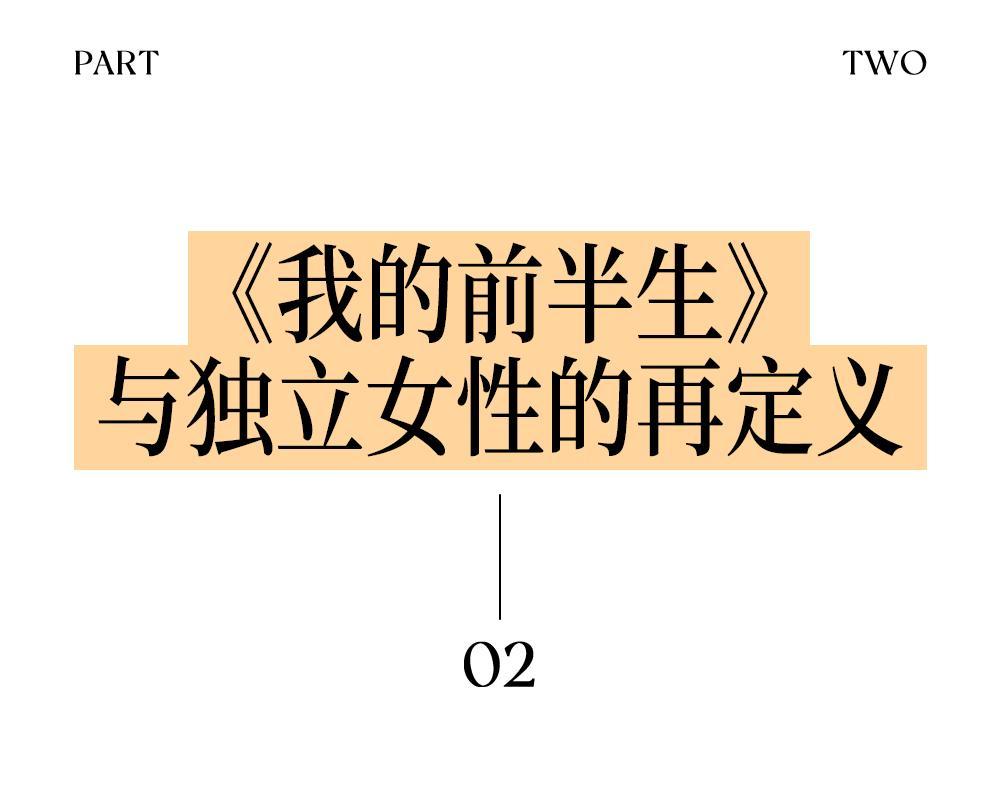
如果說《蝸居》展示了愛情如何在生存壓力下異化,那麼《我的前半生》翻紅,則是對“愛情之後”或“沒有愛情之後”女性生存狀態的探究,也是一場對獨立女性的再定義。
2017年這部劇熱播時,唐晶在當時可謂是完美的職場女強人,她穿剪裁利落的Max Mara大衣,對閨蜜羅子君說的那句「他能養得起你,我唐晶也能養得起你」,至今讓人記憶猶新,相對而言,羅子君則是一種反面教材,被丈夫拋棄後,竟愛上閨蜜男友,就該受到道德審判。

然而九年時間,評論風向卻有了改變。
首先是唐晶,她的獨立其實過於嚴絲合縫,反而成了另一種不自由——她不能示弱,不能出錯,她爲自己掙到了車子房子,但在發着高燒難以支撐時也會繼續工作,即便老闆只需要她工作8小時。她的強大,某種程度上是被由男性主導的職場馴化出來的生存方式,無懈可擊的理性,本身就是一個精緻的牢籠。
而賀涵對唐晶十年的“培養”,也被重新解讀爲一場漫長的養成遊戲。他對羅子君的關注,同樣被指出,或許是在另一個“作品”身上,重溫創造的快感,愛情退場,權力結構浮出水面。

法國哲學家露西·伊利格瑞曾在《他者女人的窺鏡》裏講,現代女性其實長期在男性話語中被定義,進而成爲客體。她主張通過「戲擬」,即有意識地模仿男性賦予女性的角色,以過度表演來暴露角色本身的荒謬性,從而解構它,建立真正的主體身份,創造屬於自己的語言——「女人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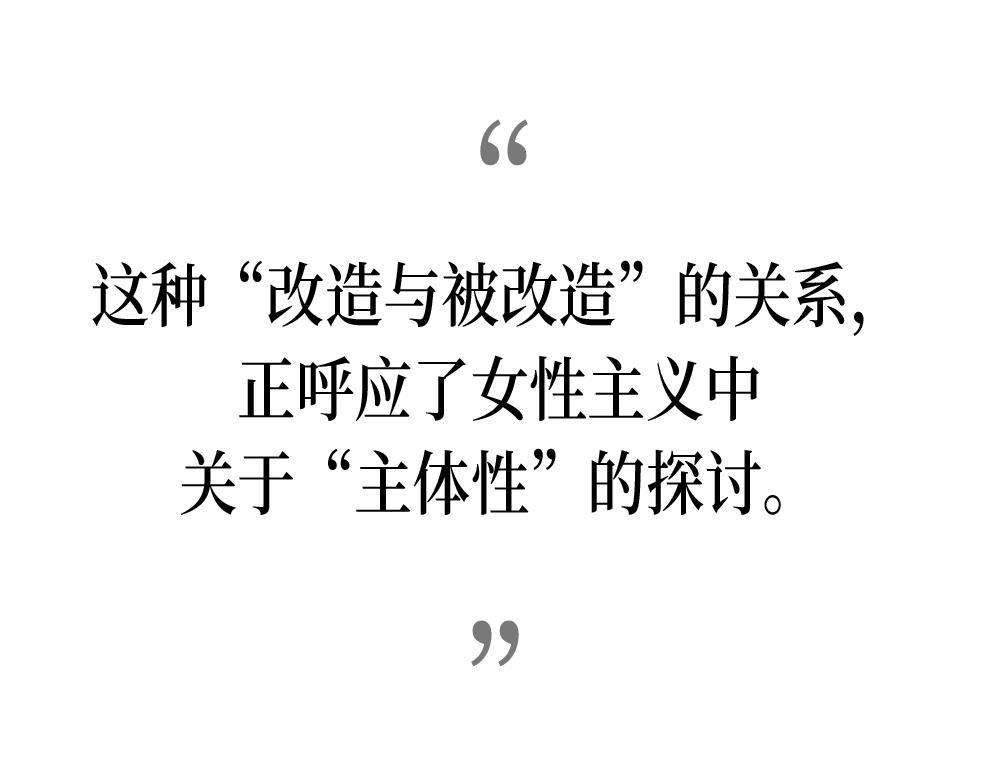
唐晶看似是一名成功的獨立女性,她在男性主導的職場裏奮力做到了頂尖,但在某種意義上,她仍是卓越的戲擬者,而非規則的制定者。她的處境反而揭示了真正的獨立,並不是固定的職業姿態或社會身份,而是擁有從容選擇的能力。

這種能力如今甚至可以體現在對主流成功路徑的偏離上,就像近年來在瑞典等北歐國家興起的一股“soft girl”風潮,很多女性開始有意識地拒絕高強度、高壓力的職業賽道,轉而選擇從事創意工作、part-time job,或將更多精力投入家庭,她們並非躺平或退縮,而是以柔和姿態重新定義何爲“有意義的生活”與“有價值的勞動”,這種趨勢同樣延展了我們對於“獨立女性”的想象。
與此同時,真正完成逆襲的,反而是羅子君。
羅子君的覺醒,始於主體性的徹底歸零——作爲“陳俊生太太”的舊身份被註銷,但她沒有變成唐晶2.0,而是在掙扎中,以一種近乎直覺的方式,摸索屬於自己的路。

她跪地爲老同學試鞋的屈辱、她對賀涵既依賴又抗拒的糾結、以及最終離開上海的抉擇,每一步都充滿反覆的度量,不符合任何“大女主”爽劇的規範。但這正是伊利格瑞所倡導的,在斷裂處生長出異質性經驗的過程,觀衆在她身上看到的,不是“我應該成爲誰”,而是“我可以如何成爲自己”,哪怕這個過程笨拙、反覆、不完美。
這些都在指引我們想象更立體的現代女性形象,也觸及了老劇翻紅的核心:觀衆不再相信完美的敘事。

我們不信海藻能純粹地物質,於是看到了她的不得已;我們不信唐晶能徹底地理性,於是看到了她的脆弱;我們不信羅子君能簡單地逆襲,於是看到了她的掙扎與反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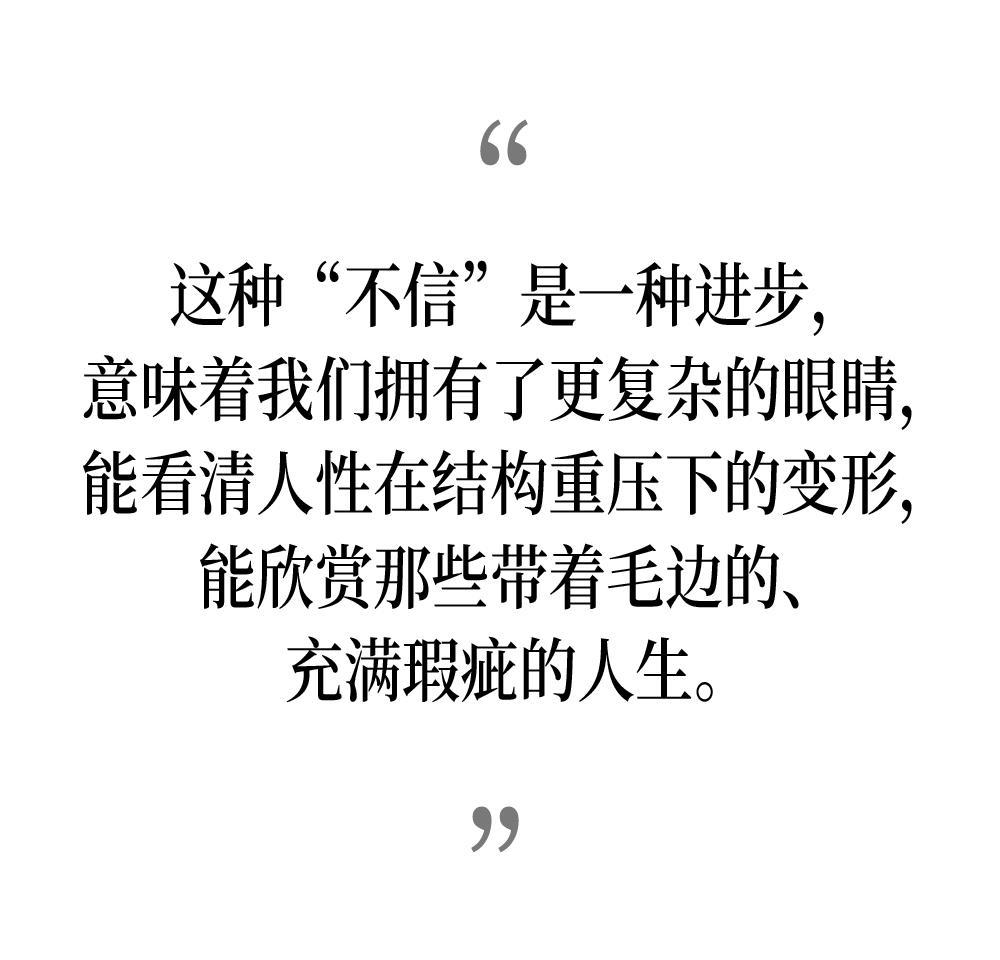
那麼,爲何是現在?因爲此刻,我們依舊處於某種巨大的“中間狀態”裏,經濟從狂熱增長進入複雜週期,愛情從浪漫敘事落入現實考量,這些老劇,恰好擁有相似的震盪,回頭去看,能找到一些共鳴以及一種確認——我們當下的迷茫,從前也被經歷過。這或許就是時間賦予舊故事最重要的意義:不提供答案,但讓問題不再孤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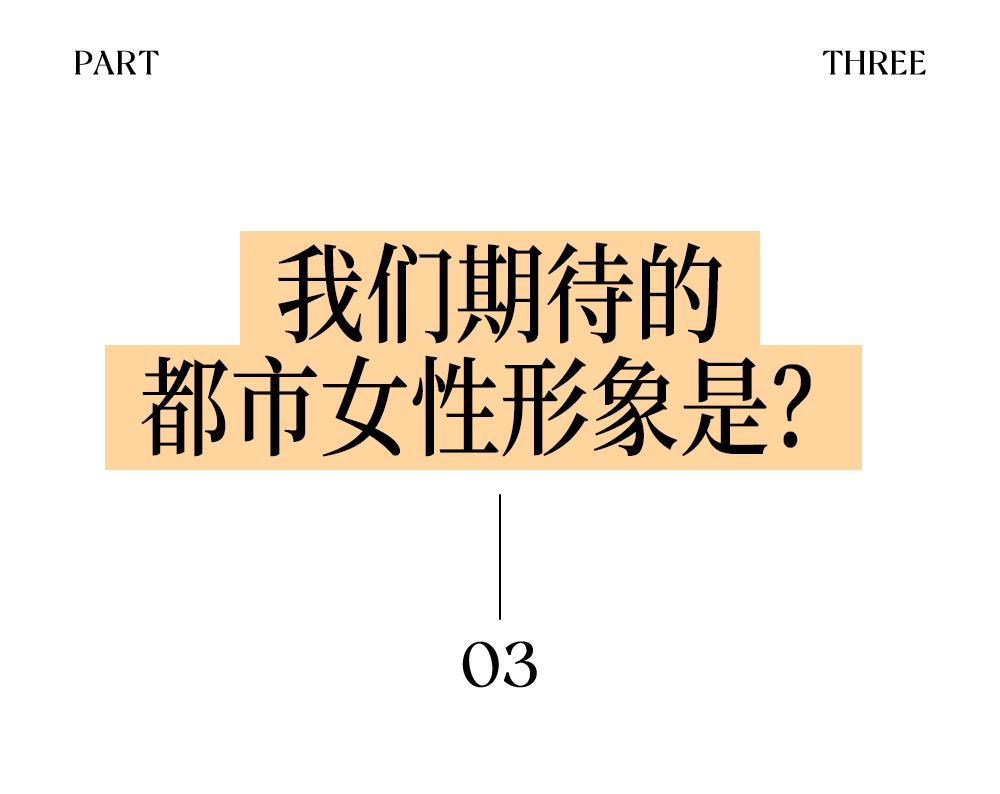
那麼,大熒幕如何爲我們創造更爲立體、更爲真實的女性形象呢?
答案是,比起對“女性”標籤的簡單運用,我們更需要看見覆雜而深邃的人性,未來的她,不必是海藻式的犧牲品,也無需復刻唐晶的獨立。她首先是一個可以充滿內在矛盾、在具體境遇中做出相應選擇的人。
而近年來,一些角色已勾勒出這種可能性的輪廓。


比如《繁花》中的玲子,在至真園的推杯換盞間,她的出場依附於爺叔與寶總,但隨着黃河路風雲變幻,玲子的韌性、市井智慧與最終獨自經營夜東京的決斷,讓她完成了從“他者故事裏的註腳”到自我敘事主體的轉變。

更進一步的探索,出現在《漫長的季節》中,李庚希飾演的沈墨,其悲劇的根源固然與男性施加的暴行緊密相連,但劇集並未將她簡化爲純粹的受害者符號。她的復仇是沉靜的,愛與恨同樣堅決,而這部劇的女性從巧雲到黃麗茹,她們的形象也都在證明,女性的故事,可以並且應該承載與男性敘事同等的重量。


先前引發熱議的臺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同樣也爲我們展現了更加豐富的女性形象。林依晨與許瑋甯飾演的簡慶芬與Rebecca,一個看似擁有“標準答案”般婚姻,一個是大齡未婚的單身精英。
故事的焦點不在於評價哪種生活更好,而在於細緻地展現兩個中年女人共享的困惑、嫉妒、未被滿足的慾望與女性之間愛恨交加的情誼,繼而啓發觀衆其實任何一種活法都不能豁免於人生的複雜與遺憾。

而我們所期待的熒屏女性形象,她所追求的“成功”不一定只能來自職場或戀情,也可以是具體的生活,可以源自如何安放自我、與原生家庭和解、在成長中尋求突破......就像許知遠說的對微小事物的關切可以超過對宏大敘事的關心。
她的慾望可以複雜,她能同時渴望事業成就、情感慰藉、物質安全與精神自由;她的角色設定,應源於具體的人格與經歷,而非“是女性就該如何”的預設;她的人性灰度也可以被確切描述,她能在職場殺伐果決,卻在情感中優柔寡斷,可以出於利他初衷,卻行至自私境地。
最終,歸根結底,當我們談論“不懸浮、有缺點、真實而鮮活”的女性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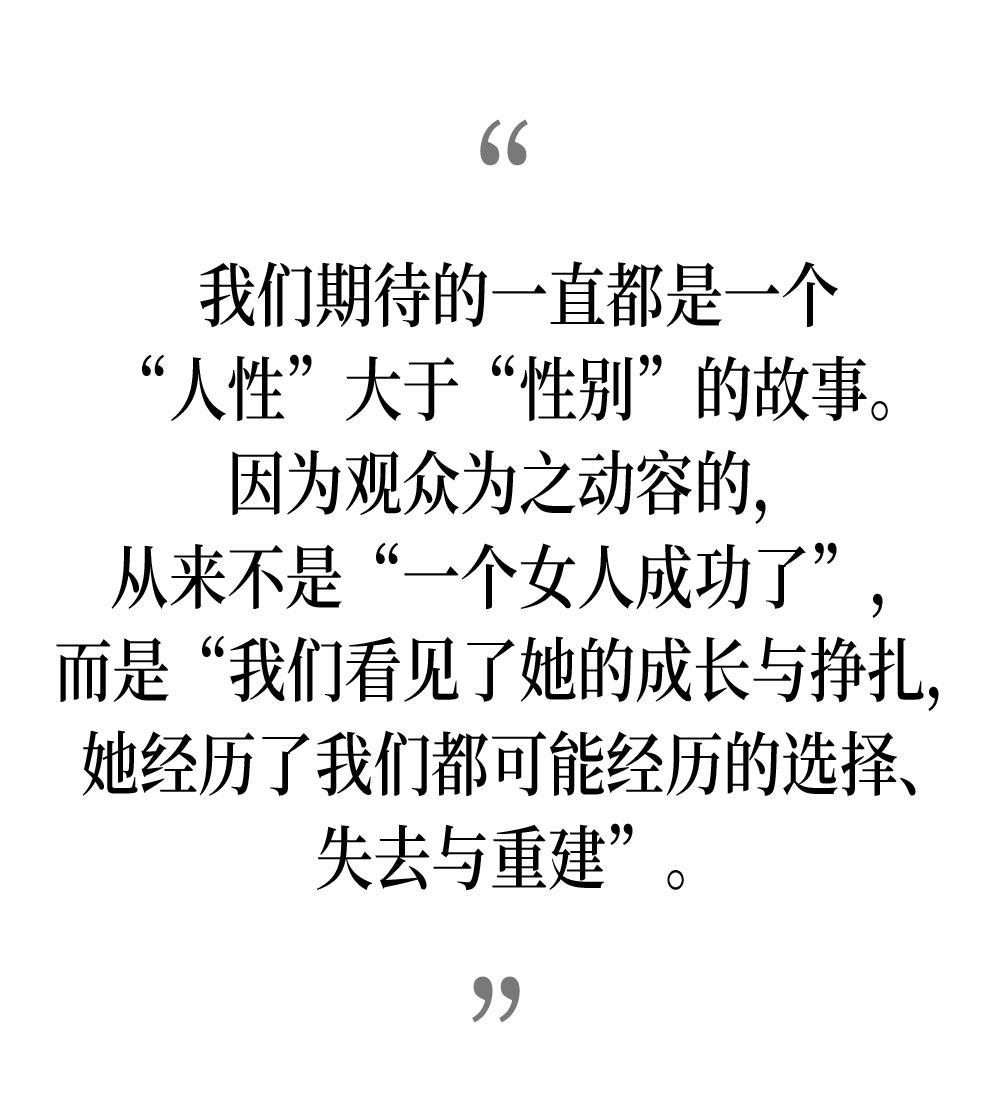

《蝸居》與《我的前半生》的翻紅,從來都不是因爲觀衆懷舊,懷舊是嚮往回不去的時光,而我們不向往2009年高漲的房價,也不向往2017年那個對獨立女性只有單一答案的時代。
我們一次次點開老劇,是因爲它們拍出了真實生動的女性角色,以及它們所記錄的困境從未真正消失,只是換了名字,換了年代,換了一批正在經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