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愛得卑微,
掏心掏肺卻換不來一句真心;
有人愛得強勢,
把對方管得死死的,
最後卻落得兩敗俱傷;
還有人愛得小心翼翼,
一遇到矛盾就躲得遠遠的。
可偏偏就有人,
能在愛情裏肆意綻放,
收穫滿滿的幸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親密關係是面鏡子,
照見最深的是你未被治癒的童年。
也就是說,
你今天的情感困局,
早在童年就埋下了伏筆。
那麼今天,
是時候看清這盤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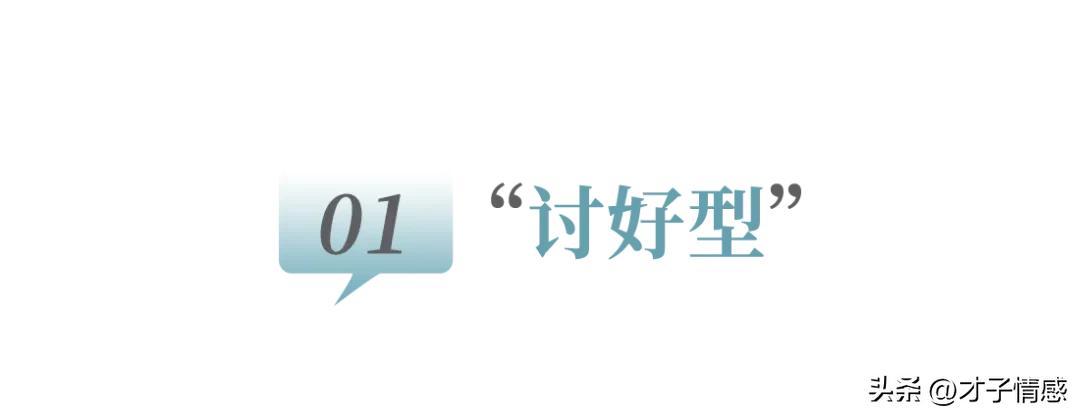
學員小林的老公某天隨口提了句
“好饞你做的糖醋排骨”。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小林特意連趕幾天工作進度,
終於有天按時下班衝去超市,
挑了上好的排骨。
結賬時趕上高峯期,
又排了半小時的隊。
儘管已經很累,
但回家後還是立刻繫上圍裙開火。
站了兩個小時腰痠背痛,
但看着鍋裏成色不錯的排骨,
她心裏特開心,
甚至能想象到老公大快朵頤的樣子。
可老公只夾了兩塊就不再夾了。
她問:“不好喫嗎?
我覺得挺香啊。”
老公也說:“挺好的。”
她不甘心:“那怎麼不喫了?
前幾天不是你說饞嗎?”
他解釋:“那會兒特別想喫,
現在那個勁過了,中午又喫撐了。”
小林覺得:
自己一早就跟你說晚上要喫排骨,
你中午還喫多,
這排骨是多不容易才做出來的你不知道嗎?
就這麼不珍惜?
於是冷着臉甩出一句:
“愛喫不喫!”
空氣瞬間凝固。
老公不再說話,悶頭扒完飯,
就躲進了書房。
兩人就此開始了冷戰。
小林很痛苦,每晚都失眠。
又是一個失眠的夜晚,
她刷到了我的“療愈”音頻,
邊聽邊跟着冥想,幾次之後,
她說眼前浮現出一個小女孩。
小女孩正努力把摔碎的碗粘好,
小心翼翼地捧給父母:
“你們看,碗沒壞……”
原來她童年時父母常常冷戰。
那次衝突的起因,
是母親特意早起,
給父親做了碗他家鄉的手擀麪,
卻被父親嫌棄“不如奶奶做的好喫”。
母親當場摔了碗歇斯底里:
“跟你媽過去!”
小林無意間重複了母親討好的模式,
認爲付出既是愛的表達,
也無意識地期待被看見和肯定。
而她老公的創傷也被觸發。
他童年時,
母親常逼他喫自己做的“黑暗料理”。
只要他稍露難色,
母親立刻收走飯菜,
冷臉說“愛喫不喫”,
讓他餓着肚子睡覺。
“愛喫不喫”對他而言是情感撤回的警報:
他表達不滿 = 失去母親的關愛。
你看,兩個受傷的孩子,
在婚姻裏無意識重複着父母的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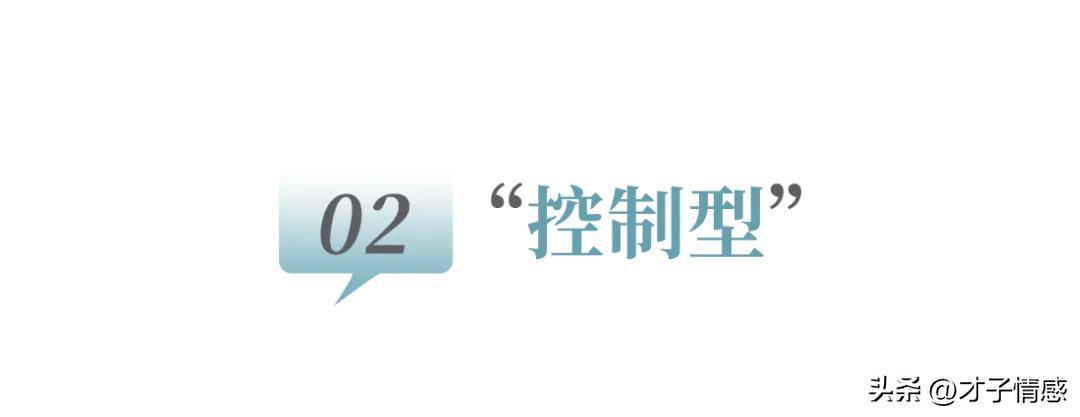
這種模式,
有時就像大家常聽到的NPD,
自戀型人格障礙的一種表現。
不久前熱播的《再見愛人4》
裏楊子和麥琳,
就是典型的這種NPD類型。
只是,楊子是目標清晰、
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的NPD;
麥琳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卻希望對方能滿足她的那種。
爲什麼愛一個人,
會變成想控制對方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呢?
這份強烈的控制慾,
其實可以追溯到嬰兒時期的全能自戀。
想想看,那個階段的小嬰兒,
完全依賴照料者生存。
他冷了、餓了、拉了、難受了,
唯一的表達就是哭。
他需要被當成一個“小國王”及時回應:
他一哭,奶來了;
一哼唧,被抱起來了……
那時,他的一個念頭,
彷彿能直接控制世界:
“我難受,我就能獲得安慰。”
如果照料者總是及時出現、安撫,
他內心會建立這樣的安全感:
“我是被愛的,
世界是穩定可控的。”
但如果他的哭聲常常被忽視,
或是等不到及時的回應,
那份無助感和恐懼,
會深深刻在潛意識裏:
“世界失控了!
我再怎麼哭喊也沒用……”
長大後,
這份對“失控”的恐懼就可能演變爲:
要獲得愛和安全感,
就必須牢牢控制住一切,
尤其是最親近的人。
對控制型的人來說,
他們會不自覺地忽略伴侶的感受和需求,
把自己的想法、
標準強加給對方。
他們的核心邏輯往往是:
“我愛你,所以我纔要管你。”
你穿什麼衣服他才安心,
你交什麼朋友他才放心,
你喫什麼他才覺得對你好……
這就像一種替代性滿足:
每一次成功的“控制”,
都讓他們重溫了嬰兒時期
“哭聲得到回應”的原始快感。
伴侶一旦違抗他們的意志,
對他們而言,
如同世界再次崩塌。
他們會冷臉、冷戰、指責,
甚至咆哮。
爲什麼反應如此激烈?
因爲你的“不服從”,
瞬間喚醒了他們嬰兒期那種撕心裂肺、
卻無人回應的,
巨大無助感和被拋棄的恐懼,
彷彿又回到了那個無助的小嬰兒狀態。
他們習慣了通過掌控一切,
來獲得那一點點虛假的安全感。
當然,理解不等於無底線承受。
不得不承認,
這種模式對親密關係是巨大的消耗。
被控制的一方會像黃聖依或李行亮那樣,
感到壓抑、委屈、失去自我,
愛意逐漸被疲憊取代;
而控制者本人,
也常常深陷焦慮,
如同緊繃的弦,
難以享受關係本身的鬆弛與美好。
伴侶的疏離或反抗,
幾乎是必然的結局。
改變這樣的互動模式,
需要控制者深刻的自我覺察和持續的成長。
而作爲伴侶,
理解其行爲背後的傷痛是慈悲,
但清晰地守護自己的邊界,
勇敢表達真實的感受,
更是對自己的負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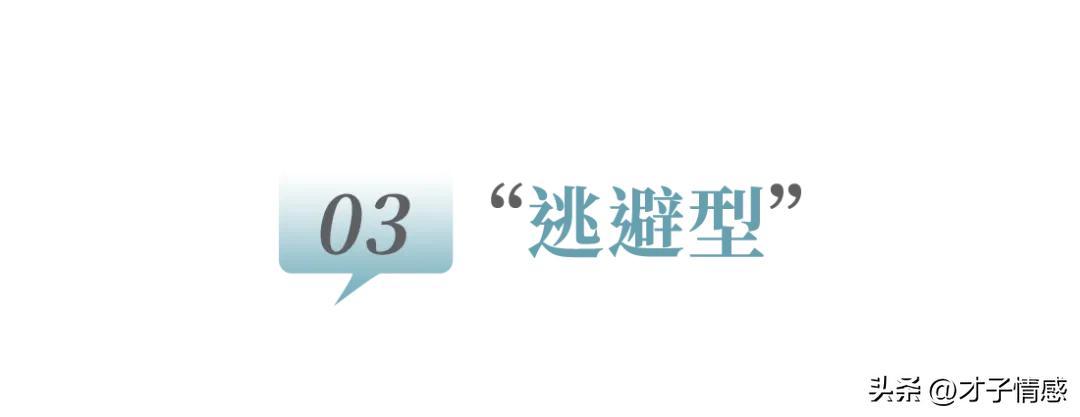
我們身邊挺多這樣的人,
可能你自己就是啊。
這是在親密關係中習慣性“消失”、
迴避衝突、害怕深度聯結的模式。
你倆見面的時候,
或者你找他聊天的時候,他挺好,
能像正常人一樣談笑風生,
甚至顯得深情款款。
可一旦物理距離拉開了,
他不會主動表達思念,
甚至不會主動找你,
就立刻變得疏離、冷淡,
甚至“失聯”。
那麼遇到衝突呢,
不管是什麼衝突,都選擇冷戰。
只是他的冷戰不是爲了懲罰你或讓你服軟,
而是源於內心巨大的恐慌。
爲什麼靠近溫暖時,反而讓他想逃?
答案往往藏在童年的暗影裏。
比如學員小青的老公,
他小時候,家裏氣氛總是壓抑的。
有次過年,親戚們熱熱鬧鬧聊天,
小小的他也想分享學校趣事,
剛開口就被父親嚴厲打斷:
“大人說話小孩別插嘴!懂什麼!”
他瞬間像被澆了盆冷水,
滿腔的興奮和表達欲硬生生憋了回去,
只剩下難堪和羞恥。
類似的事情很多:
他哭鬧時被關進小黑屋“冷靜”;
表達難過被斥責“沒出息”;
想親近父母卻被推開“自己玩去”。
久而久之,他逐漸明白:
表達真實的感受是危險的,
會招來否定、冷漠甚至懲罰。
他潛意識裏形成了這樣的等式:
袒露內心 = 被拒絕 = 受傷 = 不被愛。
愛,對他而言,
變成了一個既渴望又恐懼的存在——
既渴望溫暖,又害怕被傷害。
於是,他學會了一種生存策略:
關閉情感通道,保持距離,
依賴邏輯和獨立空間。
見面時他能“模仿”親密,
因爲那是在可控的、
短暫的安全時段內,
他調動了所有學來的社交技巧。
但分開後的線上聯繫、
日常的情感流動,
對他而言卻像踏入雷區,
他害怕說錯話,害怕暴露需求,
害怕捲入無法處理的複雜情緒。
如果你剛好是焦慮型,
跟逃避型的人相愛,
尤其是異地戀,
那簡直是巨大的考驗。
你會因爲他突然的沉默、
幾乎沒有的消息而陷入瘋狂猜疑:
“他不愛我了?他出軌了?”
於是信息轟炸、電話追問。
但這恰恰觸發了逃避者最深的恐懼,
你的強烈情感需求像海嘯般湧來,
他感覺自己要被淹沒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逃得更遠。
他可能不是不愛你,
只是他表達愛的方式,
在你看來,
是難以理解的冷淡和疏離。
改變這種模式需要,
極大的耐心和穩定的安全感。
關鍵不是把他拽出來,
而是讓他慢慢感受到:
靠近你,表達自己,是安全的,
不會被否定和傷害。
這條路註定漫長。
許多人撐不到冰雪消融的那天,
因爲激情常在等待和不解中耗盡。
但如果你認定了這個人,
並願意付出這份耐心,
你或許有機會觸碰到他冰層下,
那顆同樣渴望溫暖、
卻傷痕累累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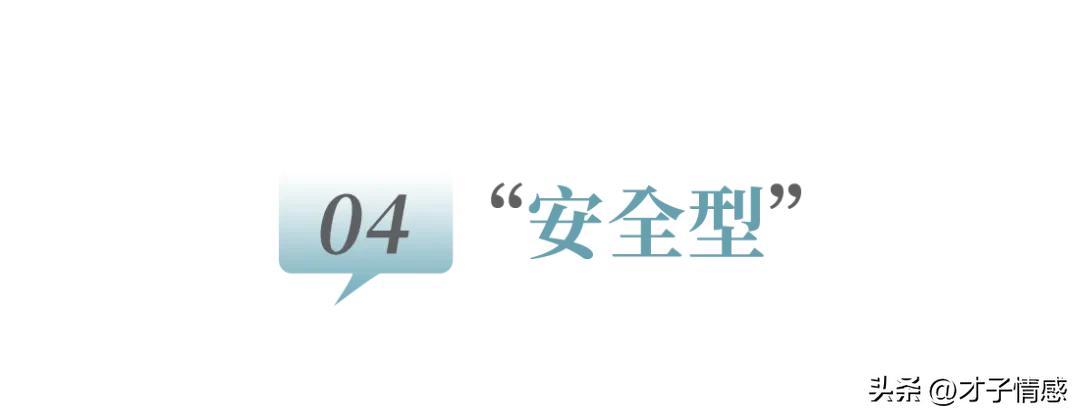
看過了前面三種在愛中掙扎的模式,
你可能會想:
難道就沒有一種關係是輕鬆自在、
讓人安心的嗎?
有的。
這就是安全型的戀愛模式。
想象一下這樣的伴侶:
當你興高采烈地分享成功時,
他眼裏有真誠的喜悅和讚賞,
不會嫉妒或貶低。
當你情緒低落、脆弱流淚時,
他不會慌張逃離或指責你“矯情”,
而是自然地張開懷抱:
“我在這裏,想聊聊嗎?”
即使你不想說,
他也能安靜陪伴。
當你們意見不合時,
他不會冷戰、控制或討好,
而是願意坐下來溝通:
“我理解你的想法,
我是這樣看的……
我們看看怎麼解決比較好?”
他享受你們的親密時光,
也坦然支持你擁有自己的興趣、
朋友和空間。
他的愛不是捆綁的繩索,
而是托住你的風,
讓你既能安心棲息,
也能自由飛翔。
他們內心擁有足夠的安全感,
源於童年時體驗過被穩定地愛着、
被及時回應、
情感被允許和接納的經歷。
比如摔倒了,父母會關心他,
問他有沒有摔疼,
是自己起來還是需要爸爸媽媽幫忙扶起來。
比如高考分數下來了,
父母會說:“不管考幾分,
你都是我們的好孩子。”
這讓他們相信:
自己是值得被愛的;
他人,尤其是伴侶,
是基本可靠和善意的;
世界是相對安全和可控的。
這份內在的安全感,
讓他們在關係中自然流露出溫暖、
包容和力量:
情緒穩定,
不易被伴侶的情緒過度捲入,
或觸發自身強烈的不安;
有效溝通,
能坦誠表達自己的需求和感受,
也願意傾聽並理解對方;
信任與獨立,
既能建立深厚的信任和依賴,
也尊重彼此的獨立性,
不把對方當作填補自己內心空洞的工具;
積極解決衝突,
視衝突爲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
而非你死我活的戰爭或需要逃避的災難。
和這樣的人相愛,
你會感到,原來愛,
可以是不帶傷痛的靠近,
是相互成就的滋養。
可能我們自己不是安全型,
也沒有遇到一個安全型。
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
無論是甜蜜還是苦澀,
都在塑造着那個獨一無二的“我”。
那些討好背後的渴望被認可、
控制背後的恐懼失控、
逃避背後的害怕受傷……
都是我們生命故事的一部分。
而看見這些類型,
理解它們的來處,
是我們打破枷鎖、
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畢竟,我們生來,
不僅僅是爲了戀愛。
我們生來,
是爲了體驗這獨一無二的生命旅程——
帶着傷痕,也帶着光亮;
帶着過往的模式,
也帶着成長的無限可能。
在愛的課題裏,
無論你此刻是哪一種模式,
都請記得:
你永遠擁有學習和改變的力量,
去創造更健康、更自在的關係,
尤其是和自己的關係。
幸與不幸,不是絕對的,
更不是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