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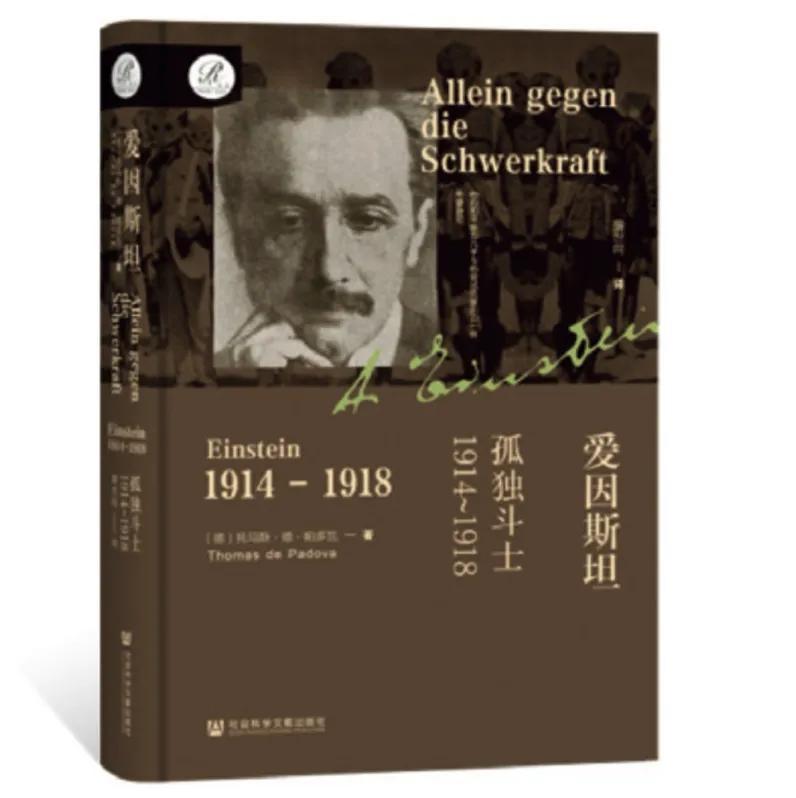
《愛因斯坦:孤獨鬥士1914-1918》
[德]托馬斯·德·帕多瓦 著
盛世同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5年11月
文 | 托馬斯·德·帕多瓦
沒有哪一位科學家像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那樣改變了我們對自然的理解。通常情況下,一位物理學家的名聲建立在被專業同行引用的基礎上,愛因斯坦卻是通過一系列間接的連鎖反應而無意中走到了國際社會的聚光燈下。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他的廣義相對論使他享譽全球。
愛因斯坦在戰後不久就獲得瞭如此盛名,首先應當歸功於他劃時代的發現。1914年-1918年,他推翻了牛頓對重力的認識,爲科學界開闢了一個關於空間、時間和宇宙結構的全新且不易洞察的領域。如果像他自己強調的那樣,我們所經歷的最美的事物是神祕的事物,那麼我們就能夠預想到,爲什麼他直到生命的終點都在思考廣義相對論,以及爲什麼它至今仍在激發人類無窮的想象。
不過,只有看一看政治形勢,才能理解他在戰後獲得的國際知名度。在柏林,愛因斯坦被說成是追求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目標的先鋒鬥士。如今,他升級爲一位楷模。這位物理學家爲未來將長期被排除在國際會議之外的德國科學界充當了“招牌”。
除了愛因斯坦,還有誰能在國外重建他們受損的聲譽呢?現在,其他國家的人把他視作不曾在世界大戰中被德國學者的戰爭狂熱裹挾的科學家。
然而,許多人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很久都不知道或不願承認的是:愛因斯坦是作爲瑞士公民來到柏林的。同所有瑞士人一樣,德法之間的戰爭在他看來彷彿是手足相殘。他在戰爭歲月裏表現爲信念堅定的歐洲人,這對他來說不是自我吹捧的理由。1918年春天,他向醫生格奧爾格·弗里德里希·尼古萊寫道,假如他作爲瑞士人採取了另一種立場,那麼他就要受到最猛烈的譴責。他早就在批評自己了。他向尼古萊解釋說,在糾正公共觀點方面,他什麼也沒有做。“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應該厭惡我的這番不作爲。”
愛因斯坦在這裏表露了一戰和二戰中的其他許多人所表現的同一種謙卑。那些爲幫助別人或影響公衆意見而有所行動的人認爲自己的行爲是理所當然的,而且知道自己原本可以做更多。
由於他在1914年8月留在了德國而不是像瑞士人那樣離開,一開始面對普遍的戰爭狂熱,他被咒罵爲“態度消極”。如果像很快就遭到“貶謫”的尼古萊那樣積極投身政治事務,愛因斯坦也許會被驅逐出德國。在戰爭最初幾個星期裏,他只希望這場噩夢能夠趕快結束。
他本可以繼續對戰爭進程不聞不問,完全埋頭於物理學。沒有人會對此感到驚訝。正好相反,他被同事們視爲學者中的例外。對馬克斯·普朗克來說,他已經是“哥白尼再世”了。
但是,愛因斯坦覺得自己放不下對公共福祉的擔憂。他的全部通信表明,戰爭破壞和人類苦難的規模之大以及國際科學往來中斷令他深感痛心。
在戰爭中,他複雜人格的一些棱面被特別地呈現出來:他強烈的同情心和近乎怪癖的思想獨立性、他的社會責任意識和他心不在焉又悵然若失的父親身份、他的無家可歸和他與猶太民族的休慼相關、他具有感染力的熱情和可能傷到他人的銳利、他勇敢而不落俗套的行爲和他對一切軍事事物的敵視、他的精英意識和他的謙虛、他的冷嘲熱諷和深深的愁緒。
他完全無法理解他的同事馬克斯·普朗克、弗裏茨·哈伯和瓦爾特·能斯特於1914年秋天在沙文主義的宣言《告文明世界書》中清楚表達的戰爭熱情。這份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德國科學界在戰後遭到抵制的宣言激起了他的反抗。作爲對此的直接回答,35歲的愛因斯坦爲和平主義的呼籲——《告歐洲人民書》——提供了支持。這是一場變化的開端。
從此,戰爭迅速地讓他參與到政治活動中。“新祖國同盟”使他發現了加入關於戰爭目標的辯論等政治討論的機會。該組織致力於實現基於和解而沒有兼併的和平,並與國外的和平主義社團保持聯繫。他自己也成長爲一個具有戰鬥精神的知識分子。
同時,廣義相對論就像一頭好久沒有等到餵食而從他身邊羞怯地跑開的小鹿。當他發覺結束這項事業的希望正在減退的時候,他便開始瘋狂地對物理學材料進行修改。於是,他在幾個星期內就完成了他建立在對空間和時間的全新理解基礎上的引力理論——這是現代科學史上最重要的個人成就。
但在1915年秋季,哪怕是這項緊張的研究也沒有妨礙他爲一本所費不貲的“祖國紀念冊”寫下他個人對戰爭的看法。在一戰期間,愛因斯坦從一位只關心科研和教學的物理學教授轉變成一位在德國現身於專業領域之外的學科帶頭人及和平主義的捍衛者。他自由的科學思考和博愛的反戰思想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在政治問題上,愛因斯坦也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他不願意接受歐洲好戰的民族主義所造成的政治現實,這種理念導致了無休止的軍備競賽。
他的想象力使他得以擺脫當下的思想禁錮,展望未來各國將會團結成一個國際聯盟。它將帶來希望:實現各民族和平共處的願望。這讓他在革命期間的柏林以及戰後的美國(特別是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早已提出類似目標)受到歡迎。對於後來在德法和解中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前身“國際知識合作委員會”中的成員身份,他在1914年-1918年也已經打下了基礎。
在這段時間裏,他的和平主義思想使他被柏林的科學界孤立了。他就像水面上的一滴油,他在給海因裏希·倉格爾的信裏寫道。一些差異,包括未曾明說的人生觀,把他與衆人分隔開來,“但始終通過純粹的知識——當然特別是物理學——維持着聯繫”。
愛因斯坦需要像理論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和馬克斯·玻恩那樣能夠傾聽自己想法的思考夥伴。但就算是普朗克和玻恩——他同樣喜歡時不時地和他們一起演奏音樂——也從來無法像瑞士和荷蘭的朋友那般親近。
這個獨來獨往、不循規蹈矩之人堅持自我,使得他在別人眼中顯得“有毛病”,他們把他的和平主義描述成“扎眼”,把他的政治觀點形容爲“天真”。他的私人通信表明,他以十足的自信和更多的直率面對政治上的不同意見者。隨着戰爭拖得越來越久,他有意識地挑起政治辯論。他的爭論具有格外寬容的特徵。
“叔本華有格言曰,‘人雖然能夠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這從我小時候起就映在我腦海裏,始終是我在面對和承受生活的艱難時的慰藉,也是寬容的一個不竭源泉”,愛因斯坦將來會如是說。
本書爲他與弗裏茨·哈伯之間常常受到誤解的關係花費了不少筆墨。哈伯非常關心他推崇的“新柏林人”及其家庭。但是,他們在科研方面沒有共同點,哈伯也不是他最親密的朋友。根據資料我們可以確認,愛因斯坦與哈伯的關係從一開始就是矛盾的,他們在1915年分道揚鑣。在戰爭的後幾年,幾乎不再有線索表明他們還保持着聯繫。
愛因斯坦對毒氣戰態度不明,這有點令人費解。與無限制潛艇戰不同,在戰爭期間使用化學刺激物和化學戰劑從來沒有成爲公共討論的對象。而在愛因斯坦看來,戰後禁用毒氣的努力還遠遠不夠。“想要給戰爭預設某些規則和限制,我覺得一點希望也沒有。戰爭本來就不是遊戲,因此無法按照遊戲規則進行。”只有“遵守規則”的戰爭才能被制止。愛因斯坦有沒有在私下裏向哈伯表示過反對毒氣戰,我們無從得知。但不大有理由認爲,他偏偏會在這個問題上對哈伯有所保留。
愛因斯坦沒有氣憤地離他而去,相反,他沒有斷絕同其好友倉格爾口中的“毒氣狂熱分子”和他自己形容的“瘋狂的野蠻人”的聯繫。基於個人經歷,他清楚他的族人從小受到的歧視。對他來說,熱衷於同化和軍事的哈伯——他的妻子在1915年5月用他的配槍自盡——也是一個悲劇人物:這位值得同情的、接受了洗禮的“猶太樞密顧問”不僅想爲德國社會獻身,還想要出人頭地。愛因斯坦認爲,哈伯的命運是“德國猶太人的不幸,是被鄙夷之愛的不幸”,直到1934年哈伯去世後,他還在給其子赫爾曼的弔唁信中如此寫道。
整個戰爭前後,理論物理學都是愛因斯坦的精神錨地。有時,他活得像一個隱士,整日閉居在他深邃的、傳記作者也無法洞察的思想世界裏,儘管他在許多年後仍真誠地面對許多問題。他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審視它們。由於不是專攻單一科目,他始終在相隔很遠的領域之間搭建橋樑。他聯想式的思想回路和數學遨遊是無法被準確描繪的。所有關於廣義相對論誕生史的描寫都會在這裏遇到極限。
愛因斯坦從來都不理解,用實驗證明他的理論會在一戰後引發如此熱烈的歡呼。多年之後,他在給物理學家馬克斯·馮·勞厄的一封信裏寫道:“如果說,我在一生漫長的沉思中學到了一點,那就是,與我們多數同時代人所以爲的相比,我們距離獲得關於基本事實的更深刻的認識還非常遙遠……以至於(對廣義相對論的)大聲歡呼不太符合實際情況。”
對此,馮·勞厄有不同看法,“後世將會設定一個不同的尺度。他們不會問這樣一個人距離自設的目標有多遠,而是會問,他給現有的知識寶庫增添了多少東西”,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努力使這樣的知識爲人類的和平共處服務。
(本文摘自《愛因斯坦:孤獨鬥士1914-1918》;編輯:許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