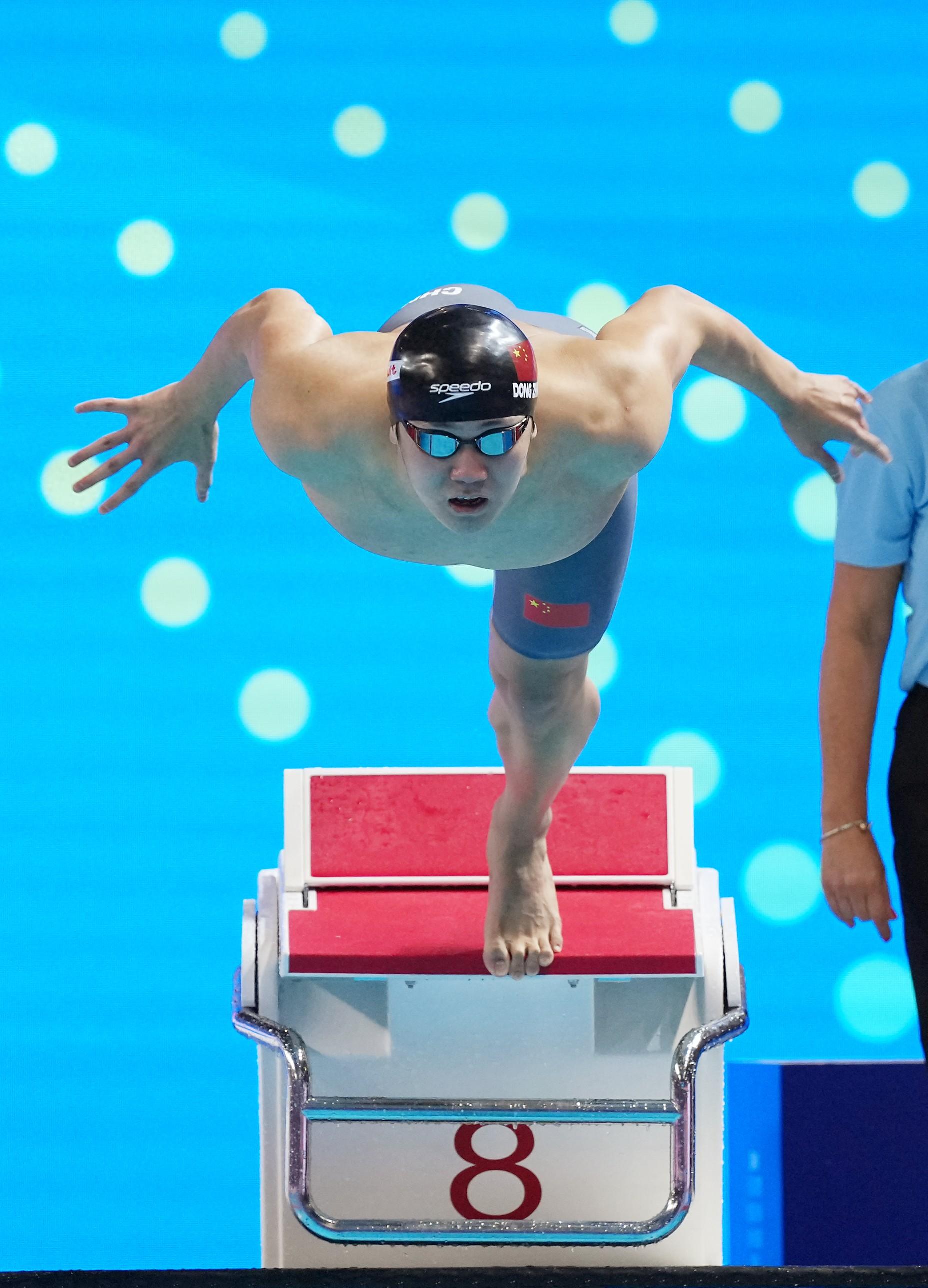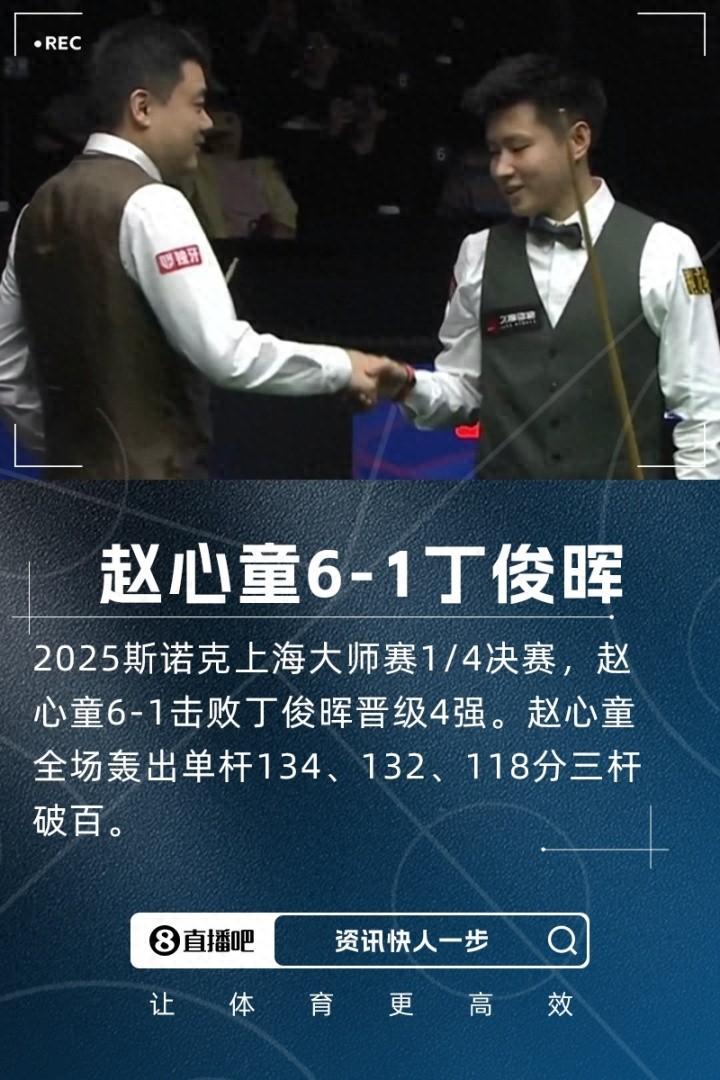拍攝上一部電影時,申奧曾在非洲取景,一個風景壯麗的地方。經過一個多月的拍攝,他從非洲飛回北京,一覺醒來,發現坐在他前面的同事一直在看窗外。他也跟着往下看,只見底下一片鬱鬱蔥蔥,或是田野,或是樹林,並無特別之處。
他問對方在看什麼,對方回道,他在看祖國的大好河山。當時還在飛行途中寫劇本的申奧立馬被擊中了,他打開電腦,將“大好河山”這四個字記了下來。後來,這四個字被具象成爲《南京照相館》中的一幕:照相館老闆老金翻動着一張張背景布,帶大家“遊覽”祖國的“大好河山”。
2025年7月25日,這部由申奧執導、以照相館爲切入點來呈現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電影《南京照相館》上映。截至7月29日,據貓眼專業版數據,該片累計票房爲5.76億元,目前位居2025年暑期檔首位,平臺預測最終總票房32億元。
開拍前,劇組花了一年時間進行籌備。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申奧數次被日軍的殘忍行徑觸痛。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個日軍將遇難者的頭顱放在鐵絲網上,在他的嘴裏插了一根菸。“日軍的暴行不限於屠殺、強姦、搶劫,還有對屍體的褻瀆、玩弄,絕對是反人類(的行爲)。”他說。

電影《南京照相館》裏,記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罪行的照片在吉祥照相館的暗訪裏洗出。資料圖
最初,劇本只設定了一條故事線,以呈現日軍屠殺的一面爲主。但隨着資料收集的進展,申奧發現,很多老照片其實是日軍的“親善照”,他們試圖以僞善的宣傳影像去矇蔽國際輿論,而以往的影視作品很少觸及這一角度。於是,他們將“親善照”與“屠殺照”的呈現並列爲影片的兩條主線。
儘管憤怒於日軍的所作所爲,但申奧在片中的表達依舊是剋制的。他有意刪除了一場由高葉飾演的林毓秀的受辱戲份,當被問及理由時,他說,就是不想拍。即使沒有直接說出緣由,但高葉完全能理解他。而對於血腥鏡頭的呈現,考慮到受衆年齡層等因素,申奧也對很多聲畫配合做了錯位處理,讓觀衆感受到殘酷的同時,“不去直面它的鏡頭”。“我也是從我自己能接受的尺度來置換觀衆的尺度。”申奧告訴南方週末。
在申奧看來,“槍”與“照相機”在結構和屬性上有相似之處,“拍照”與“開槍”甚至都是同一個英語詞彙“shoot”,兩者存在很強的關聯性。在影片的首映禮上,申奧提到,在那個八十多年前的戰場上,除了士兵的武器之戰,“還有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就是輿論戰、文化戰、宣傳戰”。他說,“每一張照片就像射向敵人的子彈。”
“拍照”跟“屠殺”的互文

片中負責在南京大屠殺中隨軍拍照的伊藤。資料圖
南方週末:爲什麼會將照相館作爲基點來講南京大屠殺?
申奧:我很早看過一個老電影,1987年拍的《屠城血證》。2023年,我認識了編劇張珂,她跟我講,這段歷史很適合拿出來再拍一遍。我就聯繫了當時的製片廠,去諮詢相關的版權,又跟張珂一起去構思了這個新的故事。
大學期間,我們都學習過膠片技術,對膠片的感情非常深。我也收集膠片相機,小時候家裏就有放大機、顯影罐、顯影液這些。爸爸曾在陽臺上拉上窗簾做暗房,教我手衝膠片。
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們是最後一批從膠片轉到數字的畢業生,畢業作業都是用膠片攝影機拍攝的。我在剪輯房裏搖着牌子,手剪膠片剪了一個多月,把我的畢業作業連起來變成一部電影。所以,無論是對膠片、對電影的感情,還是對那段歷史的反思,都是我這次創作中的重要動機。
南方週末:影片的主要劇情展現都是在照相館這個空間裏,甚至延伸到了地下室的環境中,這個場景的選擇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申奧:以小見大。鏡頭雖然對準了一個家庭的這幾個角色,但事實上當時南京是有無數的家庭在經歷這一場慘劇,希望能通過這個視角折射出整個南京城,乃至整個中國所受到的戰爭屠戮跟殘害。
南方週末:在歷史資料的選擇上,比如殺掉很多人將長江水染紅,這個有什麼考慮?
申奧:大量日軍的臺詞都來自採訪。尤其是那句“我當時如果有彩色膠捲就好了,就能記錄下這個五彩斑斕的壯麗景象了。夕陽伴隨着江面上的血水,這是多麼地壯觀吶”。這是一個老兵在回憶錄裏寫的,就收錄在張純如老師寫的《南京大屠殺》裏。我對這句話印象極其深刻,我們的苦難、我們的死亡在對方眼裏是一種軍國主義的炫耀,是他們的勝利圖騰,這個非常令人憤怒。

片中,日軍在江邊準備用機槍掃射南京平民。資料圖
南方週末:片中有很多次扣動扳機的鏡頭跟按快門的鏡頭基本上是平行重疊的,這個設計是出於什麼考量?
申奧:有一天編劇突然跟我說,“拍照”跟“開槍”在英語裏都是“shoot”。我一下就反應過來,照相機跟槍是非常相似的東西,它們都是純機械的,不需要電池就能去驅動。它的結構有耗材,也有校準;扳機跟快門都有拍攝的那一項,有不同的子彈,也有不同感光度的膠捲,從結構和屬性上來講很類似。
在劇本層面上,我們就把“拍照”跟“屠殺”變成了同一種動作的互文。在這場戰爭中,不僅有武器、軍人,也有一場非常卑鄙的宣傳戰,照相機變成了日本所謂的“撫卹官”手中的槍,這一張張照片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二次傷害,非常惡毒。
“守小禮而無大義”
南方週末:伊藤在片中的變化是他本來就會有的,還是在戰爭過程中其他軍官給他帶來的影響?
申奧:我們查閱歷史資料的時候發現,軍國主義不只是在軍人中(盛行)的思想,而是當年日本全國盛行的思想,那一代人都受到軍國主義的浸染薰陶。他們提出了“一億人玉碎”這種瘋狂的口號,用法西斯主義煽動民衆,跟軍隊一起統治亞洲、統治世界。在那個時代,日本青少年就開始被植入這種軍國主義思想。
在這個電影裏,伊藤最開始呈現出來的不敢開槍、不敢殺人等行爲,不是出於善良,而是出於一個富家公子哥不諳世事的一種懦弱。他在戰場上見證了這麼多屠殺以後,(看見的東西)就變成了他的底氣,也變成了軍官一直對他的教育和煽動(的結果)。在這個電影裏面,有兩組類父子關係,一組是老金跟阿昌的師徒關係,還有一組就是井上跟伊藤的上下級關係,都各自用一個年長男性對於一個年輕男性的教育來左右他最後的決定。
南方週末:片中有“親善照”、日本軍官寫“仁義禮智信”的情節,你想通過這些展現什麼?
申奧:我們在看資料的時候,發現有很多細節是我不曾瞭解過的,比如當時日軍成箱地打包了很多文物帶回到日本,(他們)對我們的詩詞歌賦非常感興趣,松井石根本人在南京駐守期間寫了大量的古詩。當時的日本應該是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文化崇拜,但是他們完全沒有繼承中國文化裏的大義,我們經常會說他們“守小禮而無大義”,就想通過這些劇情來展現文化戰的兩種對立關係以及這種強烈的諷刺。
南方週末:片中日本人要把景點上的磚標號,爲什麼要大量展現日軍這種對中國文化的掠奪和侵害?
申奧:我在看老照片的時候有一種很強的穿越感。那個年代的日軍在做的很多事情跟現代的人是差不多的,他們也喜歡打卡,到景點去拍照,留下“到此一遊”,寫下自己的名字、部隊番號等等。作爲侵略者,在自己踐踏的土地上做這些事情更顯得卑鄙無恥。我們展現熱戰的電影有很多,但是展現文化戰爭的部分還不夠,我很迫切地想把這一部分的細節和內容,以及我對中國文化由衷的崇敬跟熱愛展示給觀衆看。
南方週末:電影中的那些全家福,包括南京人的肖像照等,承載了你的哪些願望?
申奧:拍照是一個非常有儀式感的事,現在大家在一起聚餐、旅遊,還是會留下一張合影。但是遙想八十多年前,照相沒有像現在這麼普及,膠片又是一個比較昂貴的耗材,去拍照要全家選一個好日子,穿着打扮好,選最漂亮的衣服,用最好的狀態、髮型和笑容去面對鏡頭,留下這張可能會被傳幾代人的、在家族裏的一張照片。
照相館就不僅僅是大家的一個消費場所,而是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有儀式感的(符號),是一個個的家族史、一座城市的歷史。它代表的不僅是一條街、一座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它背後折射出來的力量是巨大的,所以才用那些最幸福的定格瞬間去反襯這些殘暴血腥的瞬間,變成他們之間的一個強烈的衝突和諷刺。
“他們認爲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南方週末:抗戰題材的影視作品很多,你在執導《南京照相館》時怎麼把握其中的尺度?
申奧:我來自觀衆,跟觀衆站在一起。從尺度上來講,我也是從我自己能接受的尺度來置換觀衆的尺度,我把我認爲可以呈現的、渲染的部分抬上來,也把我自己接受不了的尺度壓下去。只要影片最後能達到(我想要的)主題的表達、情緒的感染,我就可以完全跟觀衆站在同頻去創作。
南方週末:爲什麼會選擇高葉來出演毓秀這個角色?
申奧:我跟高葉認識19年了,大學的時候她比我小一屆。我們小的時候就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聊電影、聊未來,所以在創作初期我就鎖定了這個人選,很多臺詞都在往演員的親身經歷上去靠。
南方週末:還有選擇劉昊然來出演阿昌這個角色是怎麼考慮的?
申奧: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是朋友,很早就認識了。在日常的交談中,我發現他是一個非常聰明、敏銳、博學的人,他身上又有一股少年氣,(給人)很清澈單純的感受,尤其是眼神。在表演的時候,我們給他很多特寫,他的眼神傳達的信息很動人,也很複雜,讓人非常心疼,有的時候又很堅定,所以他的眼睛在這部電影裏面呈現出來的情緒是非常貼切的。
南方週末:片中的翻譯官在人物設計上有哪些特殊的構思?
申奧:我看了一篇關於漢奸的分析文章,裏面闡釋在那個年代所謂的漢奸都是在一種什麼樣的背景下,有一種什麼樣的心態等等。我發現,那部分人是一羣非常標準的投機分子、利己主義者,求生欲很強、缺乏信念感和家國情懷,所以他們會選擇出賣國家、出賣同胞,但他們自己不會這麼認爲,他們堅定地認爲自己選擇了正確的道路。不僅在那個時代,在和平年代,也存在這麼一部分人,他們認爲自己站在了正確的隊伍裏,而事實上他們纔是被矇蔽雙眼的一羣人。
南方週末:翻譯官的妻子和孩子被日軍掃射時,他正好有一個轉身,這是有意設計的嗎?
申奧:其實是無意的。在拍攝現場,他妻子跟他站的那個位置相隔得有200米以上,現場有日軍的吼叫聲,又有軍犬的咆哮聲,喊聲根本就聽不見。在劇本創作、演員的表演上,都是設計的他沒聽見,他自始至終都不知道自己的老婆孩子被處決了,跟老金自始至終不知道自己的老婆跟孩子遇害一樣,他們也形成了一組對照關係。
(佟金揚對本文亦有貢獻)
南方週末特約撰稿 柴瑞穎 南方週末記者 翁榕榕 南方週末實習生 馬一平
責編 劉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