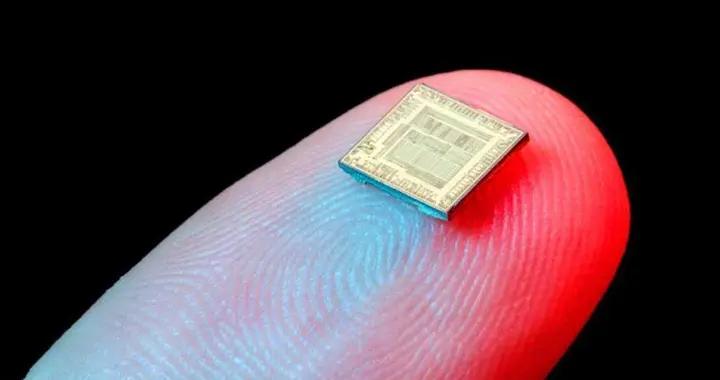近日,陝西師範大學張光偉教授和團隊提出了 AI 在專業領域演化的一個全新的範式:知識協議工程(Knowledge Protocol Engineering, KPE)。他們對當前大模型爲代表的 AI 能力發展與演進進行了總結和展望,提出了 AI 能力演化“三曲線”的觀點。第一條曲線是算力驅動,第二條曲線是事實驅動——也就是目前主流的 RAG。但研究團隊認爲,將來 AI 真正的突破可能在於第三條曲線:方法論驅動。

(來源:http://his.snnu.edu.cn/info/1016/2211.htm)
KPE 可能會在開啓第三條曲線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的思想非常直接:他們將人類專家的“隱性知識”和“工作流程”——比如一個大型數據庫的《用戶指南》或一個行業的《標準作業程序(SOP)》——系統性地設計成一份 AI 可以理解並嚴格執行的“知識協議”。
研究團隊在實驗中發現,當一個通用的大模型在 KPE 的指導下工作時,它的行爲發生了質變。它不再是進行概率性的猜測,而是像一個訓練有素的專家一樣,進行結構化的、有步驟的邏輯推理。它的每一步行動,都源自於協議的指導,這使得它的整個決策過程變得透明、可解釋且高度可靠。
所以,他們認爲:通過將人類專家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協議化,研究團隊可以有效地引導通用 AI,使其在一個特定領域內,表現出專業、可信賴的智能。
據介紹,Knowledge Protocol Engineering(KPE)研究的起點,源於他們在開發史料分析專用的 AI 智能體(Agentic AI)時遇到的一系列難以解決的難題。
研究團隊嘗試了當前最主流的技術,比如 RAG(檢索增強生成)以及 Agentic RAG,來構建能幫助歷史學家分析文獻、處理數據的 AI 助手。但他們反覆遇到三個主要的問題:(1)結果不穩定:AI Agent 的表現像“開盲盒”,有時很驚豔,有時卻犯一些低級錯誤,這種表現很難在嚴謹的學術研究中被信賴。(2)效率不夠高:Agent 完成一個複雜的分析任務,需要進行多輪的內部思考和工具調用,導致響應時間特別長。(3)成本高昂:每一次思考和調用,都會消耗大量的 Tokens,對於需要進行大規模、探索性研究的學者來說,成本難以承受。
研究團隊意識到,問題的根源在於他們只是在給 AI 提供“事實”(通過 RAG),或者給它一套“通用工具”(通過 Agent),但研究團隊從未系統性地教它一位歷史學家是如何思考和工作的。所以,他們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超越簡單的“事實投餵”和“工具授權”,將一個領域的“研究方法論”本身,注入給 AI,從而讓它的行爲變得可靠、高效、且符合專業規範?
KPE 的應用前景非常廣闊,研究團隊認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層次:
- 近期:賦能學術研究: 他們正在將 KPE 的方法論應用於更多的數字人文研究,如明清檔案、地方誌等,爲學者提供更強大的數據探索工具。
- 中期: 賦能高度監管行業: 在金融風控、保險理賠、法律文書分析等領域,KPE 將發揮巨大價值。因爲在這些行業,決策的可靠性和可解釋性至關重要。一個遵循“知識協議”的 AI,其每一步判斷都有據可查,這解決了 AI 在這些高風險領域應用的核心信任問題。
- 遠期:個性化知識助理的基石: KPE 爲在不同領域快速定製化 AI 助理提供了可能,因爲它提供了一種輕量級的、非訓練、迭代式的“賦能”AI 的方式。未來,學者、醫生、工程師都有可能擁有一個注入了自己專業工作流程的 AI 助手。
研究中,研究團隊在試圖構建史料智能分析 Agent 時曾遭遇了反覆失敗。他們給了它所有研究團隊能想到的工具——網絡搜索、文檔檢索、代碼執行。但它的表現非常不穩定,像一個有無窮精力的實習生,東奔西跑,卻總是抓不住要點。
有一次,他們讓它分析一個比較複雜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問題。它花了很多時間和大量 Tokens,從資料庫中檢索了大量相關的知識,但最終給出的結論卻犯了一個歷史學入門者都不會犯的常識性錯誤。
那一刻研究團隊似乎頓悟了:他們給了 AI“自由”,但研究團隊沒有給它“紀律”和“方法”。他們意識到,在 AI 能夠真正像人類專家一樣進行創造性思考之前,研究團隊首先需要教會它遵守領域內的“遊戲規則”。這個“規則”,就是研究團隊後來提煉出的“知識協議”。這次失敗讓他們明白,對於 AI 在專業領域的應用,約束可能比自由更重要,嚴謹的方法論可能比海量的信息更可貴。
本次論文目前是以預印本形式發佈的,所以還沒有收到正式的學術審稿意見;研究團隊正在不斷的完善 KPE 的關鍵架構,並在多個應用場景中進行測試,相關的研究論文、案例將陸續發表。但他們的預印論文已經在產業界得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共鳴。例如,凱捷(Capgemini)的全球 AI 負責人 Pradeep Sanyal 先生,在他對研究團隊預印本的公開評論中寫道:“大語言模型不需要更多的事實,它們需要更好的協議。大多數企業 AI 戰略都停留在第二曲線,但這並不能讓模型像專家一樣思考。”他認爲,本次論文所提出的“第三曲線”,即方法論增強,是關鍵的突破方向。當看到研究團隊作爲一個學術團隊提出的理論框架,能夠與全球頂尖企業 AI 戰略家的實踐觀察不謀而合時,這給了他們極大的信心和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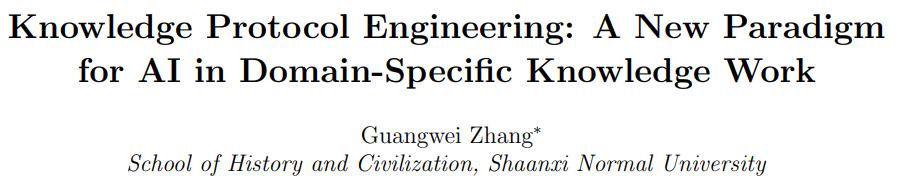
圖 | 相關論文(來源:https://arxiv.org/pdf/2507.02760)
在後續計劃上,研究團隊將主要圍繞 KPE 這個框架本身以及行業應用展開,其認爲它應該有巨大的探索空間:
第一,深化協議工程的方法論。研究團隊正在撰寫更詳細的指南,探討如何爲不同類型的知識領域——比如有些是規則驅動的,有些是案例驅動的——構建最高效的知識協議。他們希望 KPE 能成爲一種更成熟的、系統的解決方案。
第二,拓展 KPE 的應用領域。研究團隊正在積極探索將 KPE 應用於其他知識密集型領域,比如法律文本和中醫典籍的分析。他們的目標是驗證 KPE 作爲一個通用方法論的有效性和擴展性。
第三,構建開源的知識協議庫。研究團隊希望建立一個開放的社區,邀請各個領域的專家參與進來,共同爲他們的領域撰寫和完善“知識協議”。他們設想未來能有一個像 GitHub 一樣的平臺,但它託管的不是代碼,而是各個領域的、可被 AI 執行的“人類智慧協議”。
目前張光偉主要專注於學術研究。張光偉認爲 KPE 是一個值得深入挖掘的富礦,研究團隊對 KPE 的產業化前景持非常開放的態度,相信它在企業知識管理、合規和自動化決策等領域有巨大的應用潛力。張光偉還表示:“補充一下我最近在觀察 AI 相關業界討論 KPE 時最深的感觸。無論是 Pradeep Sanyal 認可研究團隊在 KPE 中所提出的‘第三曲線’,還是 Luis Dieguez 的認爲 KPE 是‘諮詢業的下一個前沿’,亦或是 Cedric Anne 的‘從 Know-How 到 Know-Flow’,這些圍繞 KPE 展開的討論都指向了一個共同的未來:AI 時代,最稀缺的資源,可能不再是數據或算力,而是高質量的、可執行的‘方法論’。”
過去,研究團隊將人類專家的智慧寫在書裏、鎖在報告裏。現在,KPE 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將這些智慧轉化爲一種“思想軟件”(Thought-ware),一種可以被 AI 大規模執行、可以不斷迭代、可以與世界實時互動的“活的知識”。
因此,張光偉認爲這次技術浪潮對研究團隊每個人最大的挑戰和機遇是:研究團隊是否能成爲自己領域知識的“協議工程師”?因爲未來可能不屬於僅僅會使用 AI 的人,而屬於那些能夠定義和塑造 AI 如何思考的人。這正是研究團隊提出 KPE 所希望開啓的對話。
參考資料:
https://arxiv.org/pdf/2507.02760
http://his.snnu.edu.cn/info/1016/2211.htm
運營/排版:何晨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