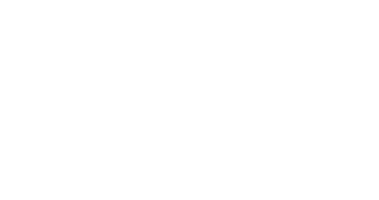在一場讀書會上,從事設計工作的上海女白領小吳說着說着就哭了。
小吳在一家外企工作,平時很忙。雖然經常加班,休息時間有限,但她還是努力分配一些時間去參加文化活動,想讓自己的思想能有所提高。
聽到嘉賓分享,過去一年讀了80多本書,小吳說,既很崇拜對方,也爲自己難受。她的想讀書單越來越長,卻安排不出時間來靜心閱讀。
事業發展、個人成長、在大城市生活的焦慮困擾着小吳。儘管她認爲自己的工作很有意義,所在的城市也是她喜歡的,朋友圈裏的美圖記錄下爲好友做伴娘、與同學去旅行、探索知名建築……但她還是覺得無法掌控自己的生活。
焦慮是一種現代病。在新書《焦慮社會》中,社會學家、清華大學教授王天夫寫道:“焦慮情緒到來時,理由從來就不那麼充分;焦慮情緒遠去時,它也並沒有那麼徹底。”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日新月異的當下,社會的“加速”感愈發強烈,人們因不適應,很容易陷入焦慮。
學業焦慮、容貌焦慮、年齡焦慮……各種個人層面的焦慮消耗了人的精力,帶來負面情緒。進而,由人組成的“組織”也會出現焦慮傾向,企業會焦慮、社區會焦慮。“焦慮社會中的社會行爲可以超越個體,形成集體行動策略,並沉澱爲社會制度,帶來更爲長久的影響”,王天夫這樣寫道。
焦慮不可避免,它的積累與驅散都不存在標準答案。在焦慮社會中,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人走出困境?
倦怠
2019年,一項覆蓋3.5萬名青年的網絡調查顯示,三種情況給人帶來的焦慮最顯著,分別是學業或事業發展達不到自己的預期(25%)、親密關係難以建立或不夠理想(16.8%)和經濟壓力(15.8%)。哪些因素推高了自身的焦慮?同輩間的比較和競爭(32.8%)、父母等其他人施加的壓力(31.7%)以及社會整體的焦慮氛圍(25.2%)排在答案的前三名。
可以看到,優績主義和加速主義給人帶來的壓力最爲直接。人們害怕失敗,希望不要錯過任何一次機會。
王天夫認爲,近年數字通信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快速發展,對個人而言,之前習慣的工作生活方式突然變快,使人很難適應。在社會層面,就呈現爲“內卷”“躺平”等心態。
2005年,有日本學者提出“信息圍牆”的概念。2008年,社會觀察家桑斯坦則提出了廣爲人知的“信息繭房”。在巨量信息的衝擊下,讓人冷靜地判斷和決策,成本與日俱增。在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人員松下東子和林裕之交流之後,王天夫發現,比較中日兩國當代社會大衆行爲與心態,“內卷”“躺平”都不少見,凸顯出快速發展的工業化社會具有某些共性。當人的心靈受到衝擊時,應有一些社會層面的思路,對人們進行支持。
王天夫2021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數字時代的社會變遷與社會研究》一文,提出對數字社會進行研究已經十分緊迫。他在文中提到,數字網絡使人們能更緊密地相互連接,人們能獲得更多更全面的社會支持,但是人們的線上線下生活也更加碎片化了,人的時間與精力被切割得很碎,疲於應付各種事項。
以醫生這個職業爲例,2021年,王天夫所在的研究團隊對來自28個省的1.3萬名醫生進行了調查。醫生們平均每天出診時間7.8個小時,另有1.5小時應對科研任務。每週的平均工作日數爲5.8天,有的醫生下班之後補寫病歷到晚上八九點鐘。爲了職業晉升,需要搞科研;日均接診26人,單人平均診療時間16分鐘,坐診工作強度大;60%的醫生對醫患關係緊張感到害怕,三分之二以上的醫生認爲媒體與輿論對醫療糾紛的報道不屬實。
現實焦慮令醫生們的職業道路產生更多的分化,離開三甲醫院加盟小醫院的醫生不少見,他們捨棄了更高的收入和聲望,願意在壓力更小的工作崗位上繼續嘗試尋找平衡。
“倦怠是現代社會過度精神暴力的必然產物”,《焦慮社會》寫道,醫生羣體對自身職業的認可和展望存在矛盾,絕大多數打算堅守,但也更不希望自己的後代“踏入同一條河”。
連接
交到更多朋友,讓白領小吳覺得改變是有希望的。讀書會上偶遇的鄧大姐說了一番話,坦率承認自己曾是被困在家庭中的消極的人,後來碰巧在一個讀書會中發現大家都有不同的人生,爲什麼不能做別的嘗試呢?搬家以後,她一直想再參與新的讀書會。當她的女兒去滑冰,丈夫在喝咖啡的時候,她用等待女兒下課的時間散步,偶遇了小吳參加的這場讀書會。鄧大姐講出自己的經歷,讓小吳意識到,他人怎麼走出焦慮,對自己是有啓發的。
一份報告提出,“療愈經濟”在2019年成爲中國的十大消費新現象。全球健康研究所在2023年發佈了一份研究報告,預測到2025年,療愈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到7萬億美元。
藝術、禪修及與城市生活有明顯差異的田園、山林景觀,給人帶來脫離固有生活的體驗。記者曾與從事美術療愈、音樂療愈的業者交流,一位療愈師表示,人們總是覺得要說出來才能解決問題,其實你還可以選擇畫出來,“不是爲了多美,而是讓你的左右腦重新對話”。
在《焦慮社會》中,王天夫認爲,情緒資本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將會逐漸超過人力資本,情緒將會成爲數字時代的市場要素。在此背景下,療愈性陪伴的廣泛出現,響應了焦慮社會的剛需。
王天夫在書中開出了應對焦慮的7種“社會藥方”,其中一點就是“拓展社會連接,建立和善社會關係”。在他看來,除了療愈經濟給人直接帶來的解脫感,更重要的是各行各業都應去思考,要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共情交流。
比如在教育領域,王天夫認爲高速發展的人工智能會導致大學教授這個崗位,以及集中授課的知識傳授方式很快消失。老師對學生能起到的指導將不再以知識傳授爲重點,而是從人生閱歷上給學生提供情緒價值。學習、成長和研究遇到了什麼困難,可以看看別人遇到同樣困難時的應對方式,思考怎樣繞開它。
“教育這個行當,離人心靈最近的那些崗位,可能會保留下來。比如幼兒園、小學老師,這些崗位一定會比大學老師更穩定。相對於大學老師,他們面對學生的學習習慣、學習方法、學習興趣,都比較細心耐心,因此在新技術背景下的職業供給會更多。”王天夫認爲,特別能共情、對人類的心靈啓迪更有經驗的人,會逐漸成爲最稀缺的人才。(原標題:在焦慮社會和AI時代,特別能共情的人將成爲稀缺人才 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