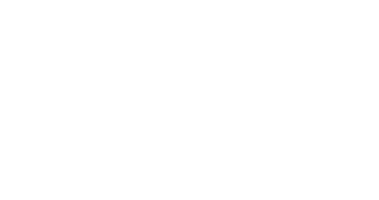張涵是上海一所大學的輔導員,同時也是學院的心理專員,過去八年,每年她都會遇到有自殺意圖的學生。2025年,她管理的200多名學生中就有7名提過自殺,考試不理想、失戀、室友矛盾等都可能讓部分學生產生自殺念頭。
在2025年年終述職時,她看到學校心理中心的PPT上寫着學生心理諮詢量同比增長了60%。
不僅是這所學校,在經濟觀察報採訪的多所高校,學生的心理諮詢需求在過去幾年均有大幅增長。江蘇一所重點高校的數據顯示,2025年的心理諮詢量比2019年增長了30%左右,顯著高於學校招生人數的增長比例。
室友矛盾找警察
張涵常常爲學生缺乏基本的社交能力感到驚訝。每學期都會有學生向她提出調換宿舍,原因常常是室友間不協調的生活習慣,但當張涵問及“你是否告訴對方你的期望”,學生往往回答“沒有,不知怎麼開口”。
她觀察到,學生們在宿舍裏幾乎都會拉上牀簾,簾子裏的人不知外面的人是否準備打遊戲,外面的人不知簾子裏的人是否在睡覺、會不會被吵到,彼此不溝通全靠猜。發生矛盾後,學生間無法自行解決,只能要求輔導員調換宿舍。
更讓她不解的是,如果調換宿舍的訴求沒有得到立刻解決,不少學生的解決方式是直接報警。面對這樣的問題,警察往往也很無奈。
還有比報警更極端的情況。因宿舍調換未能立刻解決,一名學生情急之下致電學院領導並以言語威脅,在未得到立即答覆後,該學生情緒激動,竟試圖跳樓。
在顯性衝突之外,更多的學生難以找到與同學、朋友舒適相處的方法。
鄭飛在北京一所985高校連讀了本碩。2023年,鄭飛開始讀研一,他發現自己對任何事都提不起興趣,除了上課以外幾乎記不住別的事情。漸漸地,他感到好像有一股力量輕輕掐住了他的脖子,使他呼吸不暢。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出現軀體化症狀。
2024年春天,鄭飛預約了學校的心理諮詢。鄭飛的心理壓力主要來自peer pressure(同輩壓力)。
讀研後,鄭飛與同學小林談了戀愛。兩人都讀人文學科,很聊得來。但小林成績極好,在豆瓣標記看過近2000部電影、三四百本書,每本書都會寫長評,而鄭飛只看了百十來本書。小林性格也更外露張揚,更敢表達,鄭飛則更內斂。小林一做課堂報告,鄭飛就低頭做自己的事。在私下聊天時,鄭飛也會感到壓力。
高中時,鄭飛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當時他是班上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好友。第二名非常活躍,上課會大聲回答問題,但鄭飛習慣悶頭做題。鄭飛心中有些嫉妒,又不願受到影響,就告訴自己不要去聽、不要受影響,結果“越不想聽,就越會去聽”。
這兩位同輩的外向性格,都讓鄭飛感到“邊界感被侵犯了”。他甚至產生了被威脅感:“他們都有點想扮演權威,會凌駕於我,好像他們的自我很大,會把我的自我壓扁,我會覺得憑什麼。”
這樣的同輩壓力,也出現在張涵組織的學生同輩訪談中。張涵發現學生們一方面很自大,覺得自己很行,另一方面又很自卑,看到其他同學比自己有錢、績點高、拿更多獎項時,學生們會直接用“嫉妒”這個詞,同時感到自卑。
在6次諮詢中,諮詢師逐漸陪伴鄭飛拆解開那些使他感到不舒服的細小的感受,併爲他指出大概的原因。諮詢師認爲鄭飛還不夠認可自己,自我價值表現非常低。
有時那位諮詢師會給鄭飛下一些結論,比如“請你相信,你需要認可自己”,並隨即追問鄭飛:“當我這樣說,你的感受是怎樣的?”鄭飛很喜歡這樣的交流方式:“他這樣問讓我很有安全感,我感到可以敞開心扉。此前很少有人能這樣陪我去探索。”
現在的鄭飛已幾乎擺脫那些困擾。他逐漸領悟到“就算是再親密的朋友或對象,在心理上都要保持一定距離”。養成了這樣的心態以後,他和小林的關係更融洽了。
鄭飛很感謝這段諮詢。“即使諮詢師的答案不完全是我真正需要的,我現在還時常能想起在那個狹小的空間,我被完全地尊重,漸漸打開自己。他給了我一個去努力探索的方向,逐漸地把自己的信心、認可一點一點建立起來。我也看到了兩個人對話時互相尊重的範例。”
帶病進大學
“大多數學生的問題來自未成年時期,基礎教育中缺乏對人的關注,當然不只是學校的責任,家長也在卷孩子,整體氛圍導致很多孩子的人際支持不足。”在江蘇一所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看來,整個社會太強調成績,讓教育偏離了應有的方向。
在張涵的班級裏,有不少被診斷患有精神疾病的學生,她發現患有雙向情感障礙的學生背後往往都有“虎爸虎媽”,這些學生在中學階段由於家長的極高要求患了病,帶病進了大學。
陳羽和她的諮詢師也發現了這個癥結。
陳羽是一所985大學的研三學生,2023年讀研後,陳羽就有記憶力衰退、做噩夢、語言組織能力退化等問題。2024年底,陳羽在醫院確診了抑鬱症和焦慮症。
陳羽有時會自我否定,諮詢師認爲陳羽對自己要求很高,因爲她從小到大都被人嚴苛地審視、經常被責怪,所以她總是鞭策自己趕緊把事情做好,否則可能會受到懲罰。
陳羽是長女,她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家裏,她不得不做各種意義上的榜樣,“我是家裏最省錢的孩子,成績也最好,但如果我說我不想讀博,或者我打遊戲,他們就會否定我,什麼事情都會扯到我是老大上,我從來沒感受過家庭的支持”。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家庭暴力。初中時,有次陳羽喫着早餐,父親一直在罵她,她難以忍受,重重放下飯碗,準備去上學。父親抄起掃帚就打她的腿和頭,直到硬生生把鐵桿打斷。陳羽的腿疼了一個月。她不想回家了,母親不同意,還讓她給父親道歉:“你不應該對長輩摔碗。”
“你能想象你10歲的樣子嗎?那是一個正在路邊哭泣的小孩。你現在要做的就是陪伴這個小孩。你可以對她說,‘我知道你很害怕任務沒完成,會有很可怕的後果’。你可以抱抱她,拉起她的手,告訴她其實沒關係。”諮詢師讓陳羽想象,其實她的身體裏住着很多這樣的小孩子,她們有不同的需求,各自代表着陳羽內心的某種情緒。
現在面對焦慮時,陳羽也會想象有一個10歲的小孩對她說:“你快做事呀,不然就完了!”陳羽學會了和那個小孩商量:“我理解她的焦慮也是爲我好,但那個小孩的指令和擔憂可能都是不準確的,比如災難化的後果可能不會到來。那我可以和她精確地商量,比如今天就寫500字,先玩一下,一會就去寫,行不行?”
她也從諮詢師那裏感受到此前幾乎從未體會過的溫暖。因爲壓力太大,2024年,陳羽開始大量抽菸,2025年底,她成功戒菸了,諮詢師爲她感到很開心。這種態度和母親的態度完全相反,當陳羽母親得知她抽菸後十分震驚,崩潰大哭,“她流露了出超強的厭惡,覺得我怎麼變成這樣”。諮詢師告訴她,“我也是個母親,如果我女兒這樣,我只會很心疼她”。
諮詢師緊缺
學生心理諮詢需求的增長,讓不少高校的資源供給面臨壓力。
在上述江蘇重點高校,2019年時就出現了心理諮詢資源緊張的情形。心理困擾不嚴重的學生預約排隊有時需要一個月左右。2020年後這所學校增加了專職諮詢師人數,並在校內外招聘了多名兼職諮詢師,但仍面臨專業人員緊缺的情況。
“現在心理困擾不嚴重的同學可以在10天內接受正式諮詢。”該校心理中心負責人介紹,但仍然無法實現“零等待”。學校爲此開通了“初始訪談”,讓有需要的同學可以在很短時間內接受一個較短的會談,提供心理支持。
艾莉在北京的多所高校做兼職心理諮詢師已有十幾年時間。她記得,起初一個學校的兼職諮詢師可能有七八人,現在有20多名。其中一所學校十幾年前只有五六間諮詢室,每天都會有些空閒時段;現在10—12間諮詢室,每天都會約滿。
上述江蘇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提到,現在學生的心理問題嚴重程度在變高,不是所有的兼職諮詢師都能應付嚴重的心理問題。在他所在的城市,優秀的兼職諮詢師資源不如北京、上海豐富,專業勝任力較高的諮詢師重金難求。
按照2023年教育部等部門印發的《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高校按師生比例不低於1:4000配備專職心理健康教育教師。目前還有部分學校未達到要求。在張涵所在學校,由於專職心理諮詢師缺乏,很多工作落在了學院心理專員身上,但這些心理專員常常身兼多職,心理工作負擔較重,且沒有額外報酬。
保密與上報
優質且專業的心理諮詢資源仍然短缺,有些學生接觸到不夠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反而對學校產生不信任的情緒。
陳羽本科就讀於一所211院校。2022年春天,她讀大三,學校下發了一份心理調查問卷,她記得問卷上寫了會保密,於是如實填寫了自己的狀態。過了幾天,她收到輔導員通知,讓她去單獨做一份評估。
去做評估時,她看到了好幾個同班同學,覺得很尷尬。現場的老師態度很差,問了幾十個問題,比如“你最近一段時間裏是不是感到更加抑鬱”。陳羽有時感到難以直接回答,想解釋下自己的感受,老師就會嚴厲地打斷:“你只需要回答我‘是’或‘否’。”
評估持續了20多分鐘,陳羽覺得像是被審問。這種不適的感受讓她無法信任這所學校的心理諮詢,直到讀研換了新學校後,她纔開始尋求校內心理諮詢的幫助。
阿文是東部一所理工院校的專職諮詢師。他告訴經濟觀察報,在他們學校做心理諮詢需要簽署知情同意書,其中明確了保密原則,以及保密突破的四條原則,即:存在嚴重自傷或傷人風險、出現幻覺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狀、未成年人或老年人受到侵害時,以及有法律的強制要求。
然而,在實際工作時,許多同行建議如果學生去精神科就診或者服藥時也要保密突破。阿文剛工作時,遇到一名被診斷爲抑鬱症且正在服藥的學生,並不屬於保密突破的情形。督導建議他告知輔導員,阿文當時也擔心這名學生會帶來潛在風險,於是照做了。過了很久,那名學生因爲心理訪談重新和阿文見面,說這件事讓他很受傷害,無法再信任學校。阿文道歉並和學生溝通,但仍感到很內疚。
現在阿文遇到他認爲有必要突破保密原則的情況時,會先和學生溝通,徵得學生的同意,否則,仍按四條原則嚴格保密。
上述江蘇重點高校心理中心負責人介紹,大多數輔導員知曉學生接受心理諮詢,往往是因爲學生存在較高風險,可能傷害自己或他人。他所在的學校,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與學生溝通,討論是否要告訴重要的人(如父母、輔導員),由學生自己選擇。一般不會不經溝通就直接告知。
他表示,《精神衛生法》也有相關規定,監護人有權知情。如果不告知,可能存在法律風險。“不排除個別學校或諮詢師違背倫理,但大多數情況下,核心目的不是告知別人以免責,而是希望有更多人幫助、保護學生,尤其是存在自殺風險時,需要一個支持網絡來維護安全。”
最普通的學生也應被關心
在上述心理中心負責人看來,大學生心理問題的根本不在大學,而在基礎教育和社會氛圍。“大多數學生不是在大學纔出現問題,只不過在大學表現出來而已。很多學生即使不出問題,也缺乏活力、興趣,對人生意義沒有追求。”
他認爲,整體氛圍對人的關心不足,尤其是對成績普通的學生。他提到,清華大學設立有“最普通獎”,這是好的嘗試,引導大家關注普通的羣體,關注人本身。
除了成績之外,學生還有很多需要發展的能力,例如建立積極人際關係的能力,這種能力有利於防治心理問題。這位負責人介紹,丹尼爾·戈爾曼在1995年寫《情商》時就提出要大力提倡青年一代培養情商,認爲情商是最重要的生存能力,智商只佔20%。
“但現在的教育很少關心情商,更多還是關注智商,甚至只是關注知識(不等於智商)。”他觀察到,很多前來諮詢的學生人際能力弱,難以建立良好關係,甚至出現“社恐”。
張涵也發現,有一批學生經歷了長期居家隔離,線下社交能力弱,更依賴網絡解決問題,換位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下降,遇到困難容易內耗。“比如做旅行攻略,以前會問同學,現在用攜程AI或小紅書,能不張嘴就不張嘴。”
在艾莉看來,學生願意接受心理諮詢是一種進步。
十多年前,學生就算有很多困難、甚至需要醫生的治療,也會介意去醫院精神科,諮詢師需要做很多工作,告訴學生去醫院就診能夠更好地幫助自己。現在這樣的情況在減少,在她兼職的一所學校,曾去醫院就診、帶着情緒情感障礙診斷再來學校做心理諮詢的學生,比五年前明顯變多了。
她感到,現在人們對心理和精神類問題接納度變高了,更願意去更好地照顧自己。“社會整體在進步,在一個更文明的社會,我們對幸福、對生命的感受的要求也在提升。現在我們面臨的常常不是關於生存的議題,而是關於怎樣找到生命的豐盈感、怎樣能讓自己的生命感覺更快樂。”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爲化名 原標題:心理諮詢室擠滿大學生 經濟觀察報 記者張英 劉曉諾 實習記者 田韞莘 吳育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