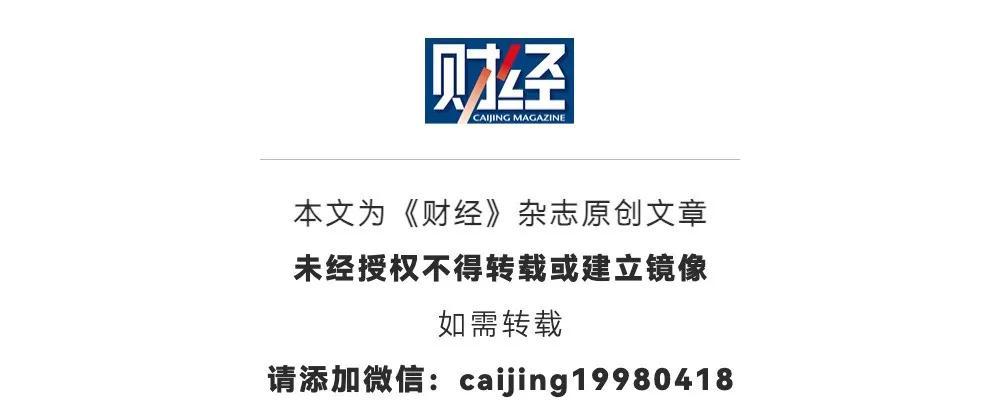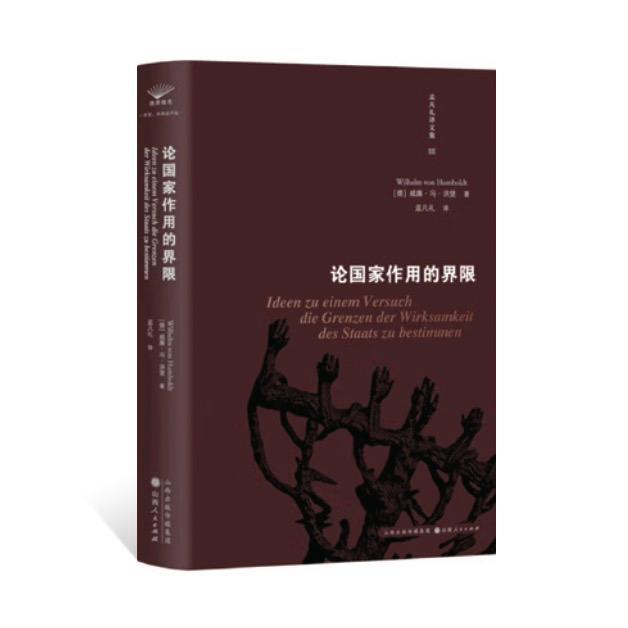
《論國家作用的界限》
[德]威廉·馮·洪堡 著
孟凡禮 譯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我一直都是從儘可能將國家干預的範圍擴至最大開始,然後嘗試一步一步地找出可以減去的地方,直到最後只剩下對安全的關心。在安全事務問題上,我現在也必須採用同樣的方法。
因此,我首先將其推至最大範圍,然後通過逐步限制,得出基本的原則。如果這被認爲有些太慢和太迂迴了,我願意承認教條的闡述恰恰需要這樣一個反着來的方法。只有通過把自己嚴格限制在像現在這樣的追問中,一個人才至少可以肯定沒有遺漏任何真正重要的東西,並且保證了原則是按照自然和連續的順序而展開的。
一段時間以來,人們越來越多地談論採取適當措施防止非法行爲,並呼籲運用道德手段。每當我聽到類似請求時,我很高興地承認,這種侵犯自由的做法在我們這裏越來越少了,而且在幾乎所有現代國家也變得越發不可能。
人們常援引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來支持這樣的政策,但是,只要他們對這些國家憲法的性質有更清晰的洞察,就會立刻發現這種比較是多麼牽強。這些國家基本上是共和國;而共和制度是自由憲法的支柱,公民熱情地擁抱共和,這使得他們對限制私人自由的有害性沒有那麼深的感受,也讓他們積極主動的性格沒有那麼大的危害。
而且,他們比我們享有更大範圍的自由,任何犧牲都只是犧牲給另一種形式的活動:參與政府事務。而現在,我們的國家一般來說是君主政體,所有這一切是完全不同的;古代人可能會採用的道德手段,無論是國民教育、宗教還是道德律法,對我們來說都不會有什麼成效,只會產生更大的危害。
此外,我們不應該忘記,在我們對古代的欽佩中,我們傾向於認爲是古代立法者英明睿智之結果的東西,大多隻不過是大衆習俗的作用,只有當其衰落時,才需要政治權威和法律制裁的支持。萊庫古所立的法律與大多數未開化民族的風俗習慣有着明顯的對應關係,這一點已經被弗格森清楚而有力地說明了;隨着這個國家往文明開化方向發展,我們只能看到這種早期大衆習俗的微弱影子。最後,我認爲,人類現在已經到達了這樣一個文明的高度,除非通過個人的發展,否則無法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因此,任何機構,只要它以任何方式阻礙個人的發展,將人們擠在一起壓成一團,在現時比在早前時代更爲有害。
即使從這些少數一般的思考中,似乎也可以得出結論,國民教育——或由國家組織或實施的教育——至少在許多方面是非常有問題的。
開篇至此,本書所展開的每一個論點,都直接指向一個總體的首要原則,人類最爲豐富的多樣性發展,有着絕對而根本的重要性(譯按:就是這一句被J.S.穆勒引爲《論自由》的篇首題詞)。但是國民教育,由於它至少要選擇和任命一些特定的教師,從而必然總是鼓勵某種特定形式的發展,無論它如何小心避免這樣的錯誤。
因此,它有着所有我們從前指出的這類積極政策必然帶來的缺點;我只需要補充一點,即任何限制,當其作用於我們本性中的道德部分時,都會變得更加直接有害;如果有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更絕對需要個人的自由活動,那就是教育,因爲它的目標是發展個人。
不可否認,當公民可以在國家中根據他的地位和處境所決定的方式自主活動,或者即便有衝突(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即當國家爲他指定的位置和他自主選擇的位置發生衝突時,也是一方面他改變自己,另一方面國家憲法也做出某種修改,此時就會產生最有益的結果;即便當然不是立竿見影的,但是揆諸所有國家的歷史,自民族性格的改變中,這種影響還是清晰可辨的。不過隨着公民從童年時代就被教育成爲公民,這種相互作用至少總是減弱了。
當然,當人和公民的角色儘可能一致時纔是有益的。但只有當公民的角色很少要求特殊的品質,也就是人可以不需要任何犧牲就可以做他自己時,這種情況纔會發生。這是我在本研究中大膽闡發的所有理念唯一追求的目標。
然而,如果人被犧牲給公民,人與公民之間富有成果的關係將完全停止。因爲儘管可以避免不和諧的後果,但人類聯合爲一個政治共同體所意欲保證的目標,恰恰被犧牲了。
因此在我看來,最自由的人性教育,始終應該是重中之重,而這種教育應該儘可能少地指向公民身份。這樣自由發展的人應該讓自己參與到國家中去;而國家憲法也要在他身上接受檢驗。只有通過這樣一番鬥爭,我才滿可指望這個民族的憲法得到真正的改善,才能消除我對公民機構有害於人性發展的所有擔心。因爲即使這些是非常有缺陷的,我們畢竟還能夠想象人的力量會起來對抗束縛,並斷言,儘管有這樣的束縛,人的力量終將保持它自己的偉大。
不過,要想讓這樣的結果變得可能,只有從來就允許人的能力在其所有天性的自由中得到發展。因爲如果人的力量從幼年起就被這種束縛所壓制,那想要讓它得到保持和擴展,得需要多麼非凡的努力?而所有的國民教育系統,由於它們總是由規訓的精神來支配的,都把一種特殊的公民形式強加於人的本性之上。
如果這樣一種形式得到清晰規定,並且儘管片面但仍然是美的,就像我們在古代國家甚至現在也許還能在許多共和國裏發現的那樣,這種教育不僅開展起來比較順利,而且事情本身也還沒那麼糟糕。
不過在我們的君主立憲制中,令人高興的是,對於人的發展來說,我們所描述的這種確定的形式是不存在的。這顯然是它們的優點,無論伴隨的害處有多少,因爲在這裏國家僅僅被視爲一種手段,不像在共和國那裏要爲此耗費那麼多的力量。只要公民遵守法律,使自己和依賴他的人過上舒適的生活,不做任何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國家就不會來打擾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這裏,國民教育,就其本身而言,儘管難以察覺,所着意的仍然是臣民或公民,而不是像私人教育那樣,着意於個人的發展,不去引導鼓勵任何特定的美德或性格;相反,國民教育旨在產生一種均平,因爲沒有什麼比這更利於產生和維持安寧,而安寧正是這些國家最渴望的目標。正如我在別處所說,這種人爲的均平,不是本身毫無結果,就是導致力量匱乏;而相反,作爲私人教育特徵的對特定目標的追求,則會通過各種各樣的相互關係,更確定地產生一種均衡,而又不犧牲力量。
即便我們完全摒斥國民教育對任何一種文化的積極促動,即便我們僅僅把鼓勵人的能力的自發發展作爲它的職責,這仍然是行不通的,因爲任何有組織的統一,總是產生相應的統一的結果,因此,即使基於這樣的原則,國民教育的效用仍然是不可思議的。如果僅僅是爲了防止兒童得不到教育,那麼在父母失職的情況下指定監護人,或者在他們貧困時爲他們提供補貼,會便利得多,危害也小得多。
此外,國民教育也未能達到它的目的,即按照國家認爲最合適的模式進行道德改造。不管教育的影響有多大,不管它如何擴展到一個人的整個行爲,伴隨他整個一生的環境仍然更重要得多。因此,如果所有這些與教育的影響不協調,教育本身就不能達到它的目的。
總之,如果教育只應該發展一個人的才能,而無需考慮賦予人性任何特定的公民品質,就沒有必要受到國家的干涉。在真正自由的人當中,所有的行業都獲得了更快的進步,所有的藝術都綻放出更加漂亮的花朵,所有的科學都拓展了它們的範圍。在這樣的共同體中,所有的家庭紐帶也變得更加緊密;父母更加熱心地照顧他們的孩子,在一種更幸福的狀態下,更能實現他們對孩子的願望。在自由人中間,人們競相向上,他們的命運取決於自己的努力,而非取決於指望從國家那裏獲得改善,此時老師們就會把他們教育得更好。
因此,既不會缺少精心的家庭教育,也不會缺少那些如此有益和必不可少的社會教育機構。但是,如果國家教育是要把某種特定的形式強加於人,那麼人們可以完全肯定,它實際上不會有任何作用,無論是對於防止違法行爲,還是對於建立和維護安全。因爲美德和邪惡並不取決於是哪一類人,也不一定與性格的某一方面有關;它更多地取決於一個人性格中所有不同特徵的和諧與否,取決於他的力量與全部喜好之和是否匹配等等。
每一項特殊性格的發展,都會片面過度,也會因此不斷趨於退化。如果整個國家都致力於某種特定的教育,那麼它遲早會失去抵抗這一盛行偏見的所有力量,以及失去用來恢復其平衡的所有力量。也許正是在這裏,我們發現了古代國家憲法變更如此頻繁的原因。每一部新憲法都對國民性施加了不適當的影響,而這種國民性格一旦發展起來,就會反過來退化,因此就必定需要又一部新憲法。
最後,即使我們承認國民教育可以成功地實現其所有目的,它也做得太多了。因爲爲了維護它想要的安全,根本沒有必要改造國民道德。但由於我採取這一立場的原因牽涉到國家對道德問題的全部關心,我將它們留到本研究的後面,先轉而考察這種關心經常會用到的一些具體措施。這裏我只需要從目前的論證得出結論,在我看來,國民教育完全超出了國家作用應予適當限定的範圍。
(本文摘自《論國家作用的界限》;編輯:許瑤)

責編 | 楊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