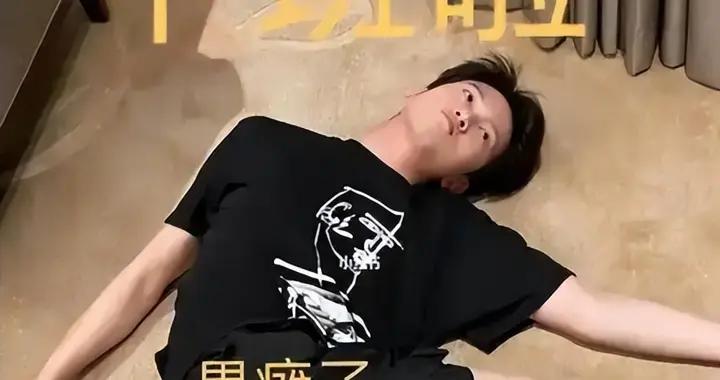說出來可能沒人信,我曾經被醫生診斷爲重度抑鬱,每天把自己鎖在房間裏,連拉開窗簾的力氣都沒有。現在不光能正常上班,週末還能約朋友爬山,誰見了都誇我狀態好。這中間的轉變,不是靠什麼神藥,而是一個聽起來特別簡單的辦法——一點點改那些鑽進死衚衕的想法。
一開始我把所有希望都放在喫藥上。不得不說,藥物確實管用,喫了大概兩週,那種想撞牆的衝動慢慢退了,晚上能睡着三四個小時,也能勉強喫下幾口飯。但醫生說得很實在:"藥能幫你暫時穩住情緒,但它無法改變你抑鬱的思維模式。"劍橋大學有項研究發現,抗抑鬱藥對中度以上抑鬱的緩解率能達到60%,但停藥後一年內復發的概率超過50%。這說明,光靠藥物是不能徹底治好抑鬱症的。

抑鬱症的病根是什麼呢?就是那些敏感、多慮、愛糾纏、完美主義的思維方式。比如同事隨口一句"這個方案再改改",我能琢磨一整夜,認定他就是看不起我;領導誇了別人一句,我就覺得自己在公司徹底沒前途了。有次看到心理學家李宏夫說的,抑鬱症患者的思維就像裝了放大鏡,壞消息會被放大十倍,好消息卻像漏網之魚,怎麼都抓不住。這話簡直說到我心坎裏。
真正的轉折點,是偶然看到王陽明那句"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那天我盯着這句話看了很久,突然反應過來:我心裏的"賊",不就是那些非黑即白的念頭嗎。比如認定"必須做到完美,否則就一文不值",比如覺得"別人稍微冷淡就是討厭我"。這麼多年來,我不就是一直被這種思維方式控制着嗎。

我開始試着用《情緒自救》書中教的"念頭記錄法"。每次陷入煩躁,就把腦子裏的想法寫下來,旁邊再寫一句"如果是朋友遇到這事,我會怎麼勸他"。
剛開始特別彆扭,寫着寫着發現,原來我對自己比對誰都苛刻。後來又看了《抑鬱症打卡自救》,跟着裏面的"微小行動清單"做,每天只要求自己做三件小事:出門曬十分鐘太陽、給盆栽澆次水、睡前寫一件當天的"小確幸"。這些事聽起來不起眼,但堅持下來,就像給生鏽的齒輪上了油,生活慢慢能轉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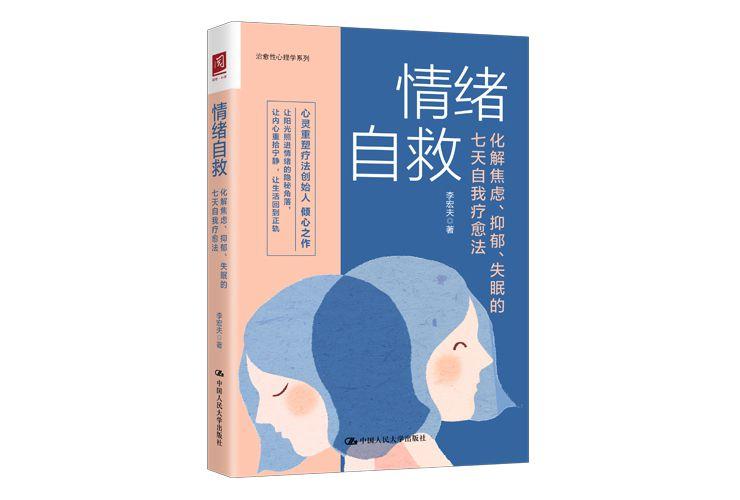
這過程裏,我還摸索出幾個管用的方法。
第一個是練習正念。不用打坐,就是喫飯的時候專心嚼,走路的時候認真看腳下的路。剛開始腦子亂得像菜市場,練了一個月,發現自己能在煩躁冒出來的瞬間,輕輕對自己說"哦,又胡思亂想了",然後把注意力拉回當下。有研究說正念能增加大腦前額葉皮質的活躍度,這部分正好管着咱們的理性,難怪練着練着,沒那麼容易鑽牛角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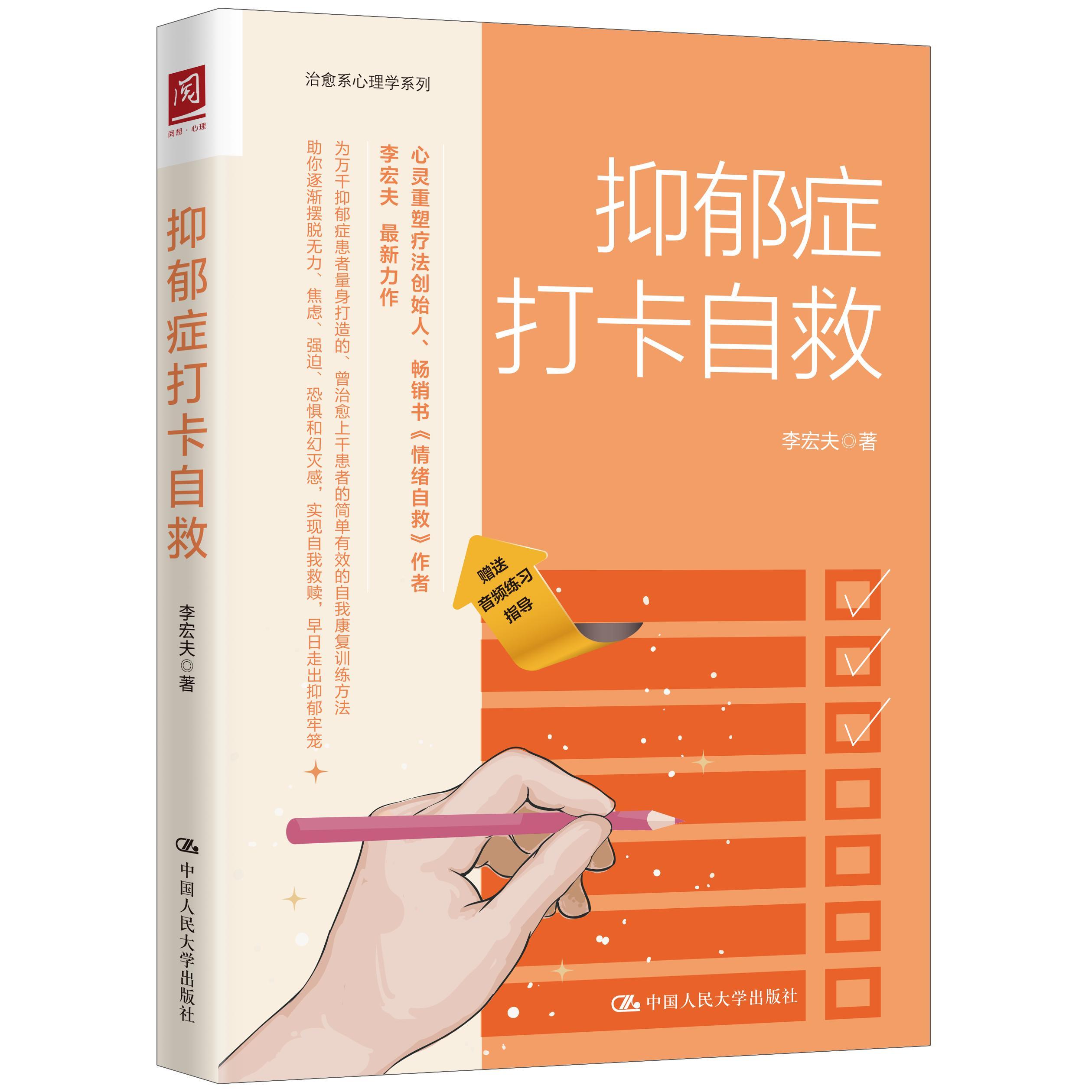
第二個是運動。別想着一上來就跑五公里,我剛開始只是每天爬三層樓梯。後來慢慢改成快走,每次四十分鐘。出汗的時候,感覺心裏的堵得慌好像能跟着排出去。大量研究顯示,運動時大腦會分泌內啡肽,這種"快樂激素"雖然不能根治抑鬱,但能幫着打破"越不動越消沉"的怪圈。
第三個是讀傳統文化經典。不是讓你啃文言文,我看的是帶註釋的《論語》和《道德經》。看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就提醒自己別總盯着別人的態度;讀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就學着接受"差不多就行"。這些慢慢幫我重建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原來生活不是隻有輸贏,過得去本身就是一種本事。
現在的我算不上完全"痊癒",但已經能和那些負面念頭和平共處了。就像天氣總有陰有晴,我不再奢求永遠晴空萬里,而是學會了在下雨時給自己打把傘。這世上哪有什麼速效藥,能治好心病的,從來都是願意一點點改變的自己。願意一點點的接納自己,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