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註相關文獻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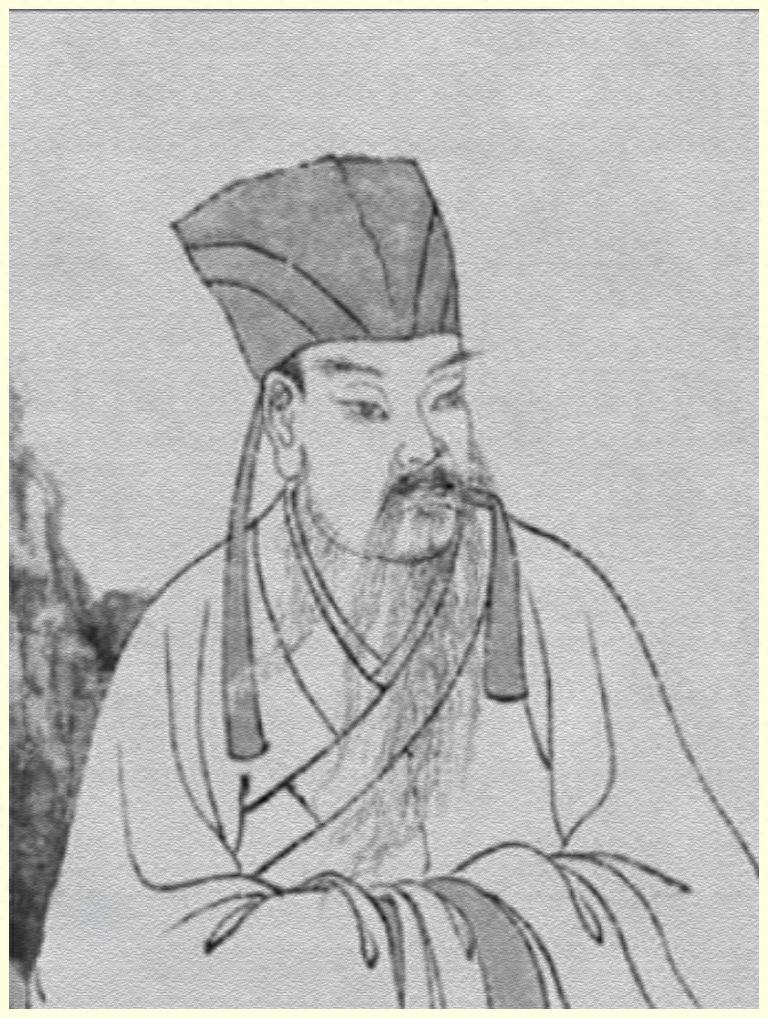
(劉攽)
劉攽和王安石的關係非常好,您知道王安石這個人私底下就不太喜歡和人聊天,性格比較高冷,但是隻要見到了劉攽,那就是相見如故,一聊就是一整天。
王安石做參知政事,就是副宰相的時候,有天在家喫飯,飯喫了一半,劉攽就跑到王安石的家裏去找王安石聊天,王安石說我喫飯呢,等我喫完我跟你聊,於是王安石就讓家裏的僕從把劉攽迎到了書房,僕從給他沏上熱茶,送上點心,僕從就走了,劉攽就在王安石的書房中小憩,稍作等候。
王安石的書房,很雅緻,佈置的很不錯,劉攽轉悠來轉悠去,就轉悠到了書桌上,他一眼就看到,硯臺的下邊壓着一張紙,拿起來一看,原來是王安石寫的一篇議論軍事的文章。
文章好壞咱們先不說啊,咱們且說,劉攽這個人,他記憶力非常強,但凡是文章書籍,只要看過一遍,必然過目不忘,所以兩三分鐘時間,他就把王安石的這篇文章給背了下來,背完之後,他就把文章又放回硯臺下邊,當做自己從來沒動過。
接着書房他也不待了,因爲他覺得,書房是很私人的地方,自己也是朝廷官員,以朝廷官員的身份來拜訪王安石,最好還是在比較公開的地方交談比較合適,所以他就退出了書房,在廊下等候。
王安石跟劉攽感情很不錯,劉攽一來,他怕故人久等,趕緊扒拉飯,風捲殘雲一般喫完了,立刻到廊下和劉攽攀談起來。
兩個人相談甚歡,談天說地,聊了一會之後,王安石就隨便問,說老劉啊,最近寫沒寫文章啊?
劉攽則說,真巧,自己正好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兵論》,是議論軍事的。
劉攽說完這一句,又接着把《兵論》中的內容全都陳述給王安石聽。
其實,劉攽最近根本沒寫文章,他說自己寫了《兵論》,還長篇大論的講給王安石,其實就是他剛剛在書房裏看到了王安石那篇論兵的文章,他背下來了,他就當成自己的講給王安石聽。
那正常來講,王安石肯定會認爲是劉攽進了他的書房,看了他的文章,所才說了他的詞,但是古人的思維和我們的思維不盡相同,王安石只會覺得,劉攽是不會到自己的書房的,就算進入了,也不會亂動亂碰,更不會去閱讀自己已經壓在硯臺下的文章。
所以王安石就感覺,自己對軍事的看法,和劉攽的相同了,擱今天話說就是撞衫了,所以劉攽走了之後,王安石非常不開心,他把那篇文章從硯臺下抽了出來,撕了個粉碎。
爲什麼呢?因爲王安石這個人吶,平素追求標新立異,總是要發表和別人不一樣的見解,如果有人和他見解相同,他就會認爲這個見解,是庸俗的,所以他纔會如此難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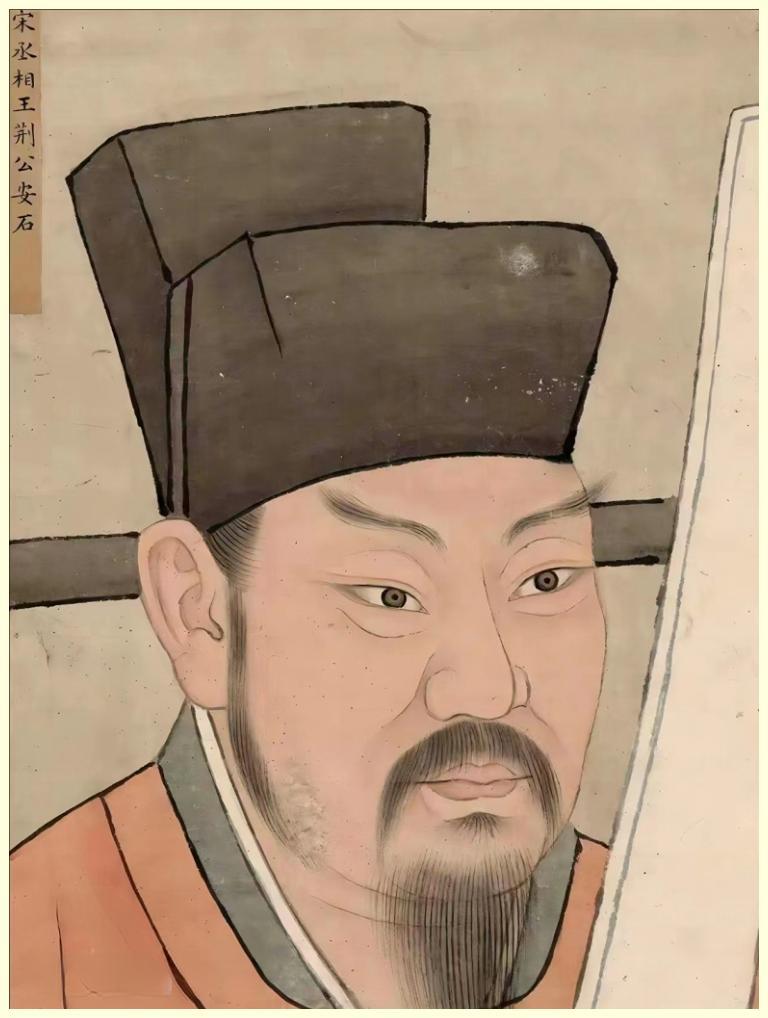
(王安石)
又有一回,王安石和劉攽聊天,我們知道王安石變法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那就是他要大力的發展經濟,他要掙錢,所以他平時很喜歡談論生財之道,民間有一個趨炎附勢的小人抓住了王安石的這個心理,就找到王安石,說大人我有一計,把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排光,然後把這塊土地改爲田地來種植,那一定能賺不少的錢。
水泊梁山,就是山東省濟寧市梁山縣境內的一個地方,《水滸傳》裏宋江起義之所。
王安石一聽,認爲這是個好辦法,非常的開心,但他隨即想到一個問題,他就一邊思考一邊唸叨,說把水泊梁山的水排光了改爲土地,用來種地,這倒是好辦法,可是問題是,排出來的水要放到哪裏呢?
當時劉攽正好在王安石身邊,劉攽當即說道:
那還不好辦麼?在水泊梁山的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的大坑,把水排進去不就得了。
王安石一聽,哈哈一笑,知道劉攽是在笑話他,終於打消了這個想法。
爭論以智慧收場,而非權力壓制,無論如何,宋代的士大夫,還是擁有更爲理性的傳統。
劉攽是北宋人,慶曆年間的進士,地方上做過知州,官職最高到中書舍人。
當然他有段時間還負責編修國史,所以他也是北宋著名的史學家。
編修國史的時候,劉攽有個同事,叫做王汾,倆人是平級。
可是有一天,劉攽卻跑到王汾的家裏,畢恭畢敬的拜見王汾,說王大人,祝賀你啊,你該換新官服了。
換新官服的意思就是,劉攽說王汾升職了,升官了。
劉攽來祝賀王汾,王汾則是一頭霧水,他說劉大人您這是什麼話啊,你祝賀我升官,可是我從來沒有得到升官的消息啊。
劉攽說那不對啊,早上閤門使,也就是負責宮廷禮儀傳達的官員已經通報了消息,您還是趕緊去問問他吧。
王汾一看,這劉攽不像是開玩笑,立刻就跑到宮裏去詢問閤門使,結果閤門使也是一臉懵,說我從來也沒得到過旨意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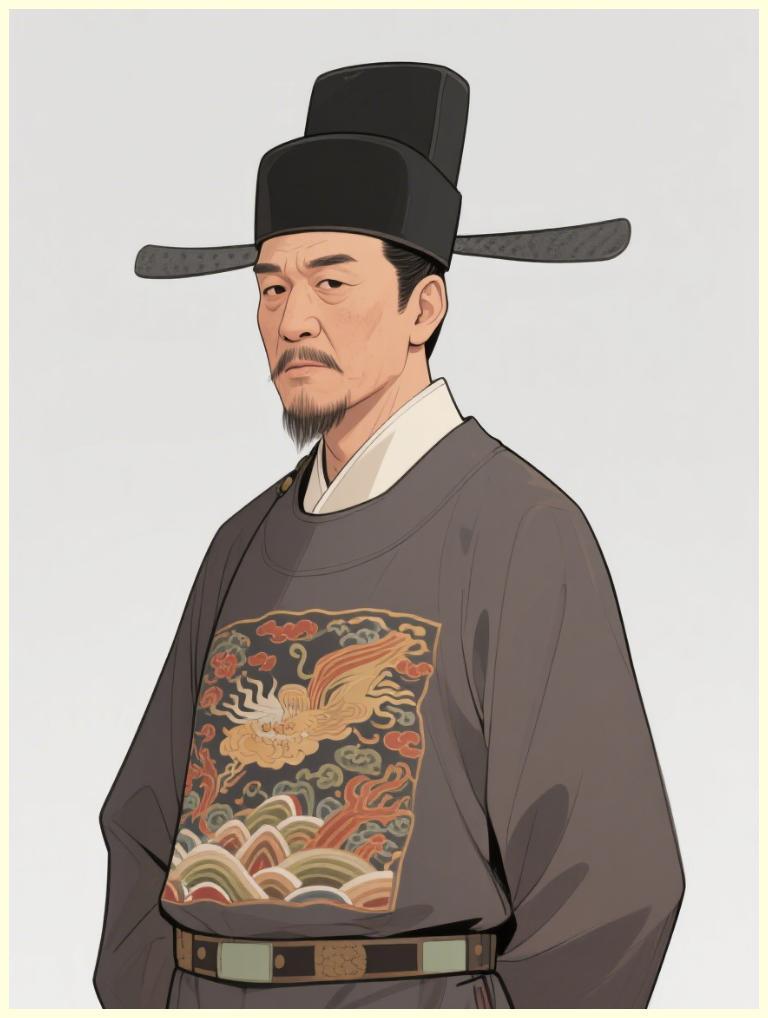
(王汾)
王汾又問,讓我升官的旨意沒有,那有沒有別的旨意?
閤門使說,別的旨意倒是有一個,那就是皇帝今天放出一個命令,這以前吧,咱們大宋朝的王公勳貴的墳墓,不允許用紅色作爲裝飾,但是現在皇帝說可以了,可以讓他們用紅色來裝飾墓室,也可以用紅泥來塗抹墓牆。
王公勳貴的墳墓,簡稱王墳,這個時候王汾才明白,原來劉攽是在戲弄他,人家皇帝明明說的是王墳可以添紅,王墳和自己的名字王汾同音,劉攽就拿諧音梗來誆騙自己升官了。
劉攽還愛好寫詩,和蘇軾也有往來,並且關係匪淺,還因爲同蘇軾唱合詩作而獲罪,當時蘇軾反對新法,被貶謫流放,跟蘇軾有來往的人,蘇軾的好朋友啊,都跟着喫瓜落,劉攽也是其中之一。
後來到了元祐年間,兩個人又都返回了京師爲官,而且還是在一個辦公室裏。
所以劉攽和蘇軾就經常閒聊,有一次劉攽就跟蘇軾講了一個故事,說以前,有一個盜賊,他闖入了一戶百姓家中,沒偷別的,只偷走一卷書就跑了,這書呢,是一個舉人寫的,裏邊基本上就是五言詩,七言詩之類的。
這盜賊偷了書,就拿到當鋪裏去賣,當鋪的老闆呢,他知道這個人是盜賊,但是他沒有聲張,而是把書收了下來。
爲什麼呢,當鋪老闆也是個讀書人,識貨,他一看這書,這詩集寫的挺好的,他就買來收藏了。
結果,第二天這盜賊就被抓了,被抓之後,自然要供認偷盜的書籍銷贓何處,衙役們直接就找到了當鋪,從當鋪老闆的手裏把這本書拿走了。
書倒是不值錢,但是屬於贓物,必須收掉。
可這當鋪老闆啊,也是一個癡人,他竟然花錢賄賂衙役,只求可以在書被沒收前,抄錄一下其中的內容。
當鋪老闆說,我太喜歡這些詩了,想自己也寫詩,順便和書中的詩一同唱和,用現在話來說等於是同人或者二創。
結果,這個請求被衙役拒絕了,衙役的理由是,這是賊贓的詩,不能唱和。
劉攽的這個故事,其實意有所指。

(蘇軾)
這本書中的詩,指的就是蘇軾的詩。
而當鋪老闆想要抄寫這些詩,其實就是在影射自己當年唱和蘇軾的古詩而被連累處罰。
衙役說,贓物詩不能唱和,其實就是在暗諷蘇軾的詩水平平庸,根本用不着唱和。
劉攽說完,蘇軾也給劉攽講了一個故事,蘇軾說,孔子當年有一次外出,他的弟子,一個顏回,一個子路正巧遠遠看到孔子走過來,兩個弟子不去拜見老師,反而連忙躲避。
子路的身手比較敏捷,一下子就爬上了樹,而顏回就比較慢了,環顧四周,他無處可藏,只好跑到一處石經幢後藏了起來。
石經幢,就是一種刻有佛經的石柱。
孔子沒有發現這兩個弟子,順着道路逐漸走遠,但是顏回藏在石經幢後的事情,很快就傳開了。
大家就議論,說這個石經幢啊,被顏回當做躲藏孔子的柱子,那就有了特殊的意義,所以不能再叫石經幢了,而應該叫做避孔塔。
蘇軾爲什麼要說這個石經幢被叫做避孔塔呢,很簡單,因爲避孔塔的諧音就是鼻孔塌,而當時劉攽正好患了一種病,這種病就導致他的鼻子是塌陷的,蘇軾是藉着這個諧音梗來嘲笑劉攽,順便還以顏色。
其實這也是宋代文人的一種生存智慧,用典故和幽默化解政治創傷與疾病折磨的痛苦。
這些看似輕鬆戲謔的軼事,如同一扇窗戶,讓我們得以窺見宋代士大夫精神世界的斑斕一角。
在劉攽與王安石,蘇軾的交往中,我們看到的遠不止文人的雅趣與機鋒,更能區別於傳統敘事,看到古人更爲真實生活的一面。
讀這篇文章,我們感覺劉攽是個怪人,做事比較不守規則,還有點叛逆,但其實他一生潛心史學,治學非常嚴謹,這又着實讓人想象不到了...
參考資料:
《東軒筆錄》
《後山叢談》
李全德.《資治通鑑》長編分修問題新探.史學史研究,2025
王豔軍,朱富銘.論蘇軾與元祐祕書省職官的詩歌唱和.河北經貿大學學報(綜合版),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