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註相關文獻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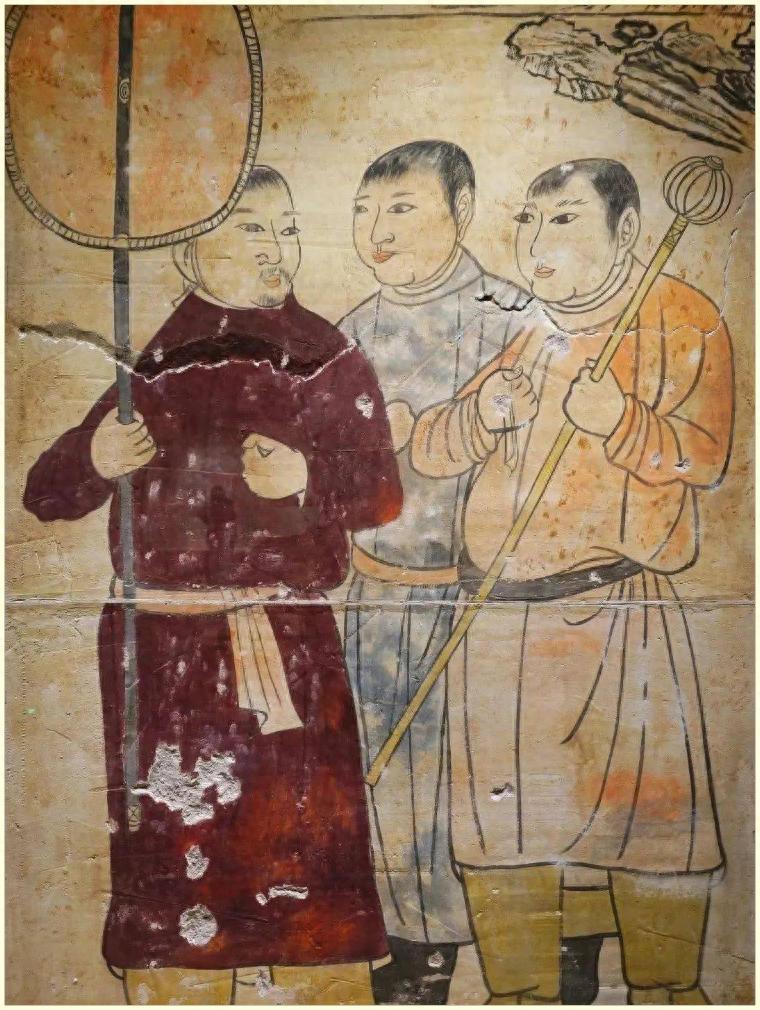
(契丹壁畫)
趙德均想在契丹人的扶持之下做皇帝,但是遼太宗耶律德光並不買他的賬。
既然做不成皇帝,那其實可以不投降,但是問題是,趙德均把多年家資已經給了契丹人,自己的王牌部隊銀鞍契丹直,也在耶律德光的授意之下被消滅,他已經沒有退路了。
沒辦法,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投降契丹,在契丹做個武將。
到了契丹之後,趙德均決定,不能就這麼放棄,至少要保證自己下半輩子衣食無憂,所以他要爲自己找個靠山。
找誰呢,思來想去,趙德均決定投靠當時的契丹太后述律平,也就是耶律德光的母親。
述律平耆德碩老,在契丹很有地位,如能拜入述律平門下,那下半輩子就算是有保障了。
只是,趙德均從來都是智商不高,他哪兒知道,述律平雖然老,但是並不糊塗,不僅不糊塗,甚至比耶律德光心思還要縝密,還要有手段。這位大遼皇后,太后的傳奇人生,在歷史上簡直是獨一檔的。
我們知道,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是公元926年死於遠征渤海國返回的路上,老皇帝一死,新皇帝的選拔和繼承工作,就由從皇后升級爲太后的述律平來主持,出於種種考量,述律平放棄了長子耶律倍,而選擇了次子耶律德光即位,只是這種行爲,必然會招致大臣們的普遍反對,尤其是契丹國家中的那些推崇嫡長子繼承製度的漢臣,所以爲了消滅反對聲音,述律平開始對朝廷的文官武將們進行大肆的清洗和屠殺。
但是我們想,就算述律平是統治階級,她也很難說在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情況下,莫名其妙的把大量的臣子都殺掉,這會激起恐慌,引起成片的反抗,所以爲了殺人,她找了個理由,那就是:
爲我達語於先帝。
我殺你們,不是爲了別的,只是因爲你們都是先帝身邊的近臣愛將,如今先帝西去,在另外一個世界好不孤單,我把你們殺掉,不過是爲了讓你們早日見到先帝,可以陪伴在先帝的身邊。
有個叫做趙思溫的大臣,述律平如法炮製,也要把他殺掉,讓他去陪伴先帝,結果趙思溫反脣相譏,他說:
太后是先帝的妻子,是先帝最親近的人,先帝如果想我們有一分,那想太后您就有十分,既然如此,如果您能做到從容就死,去陪伴先帝,那我這做臣子的也一定也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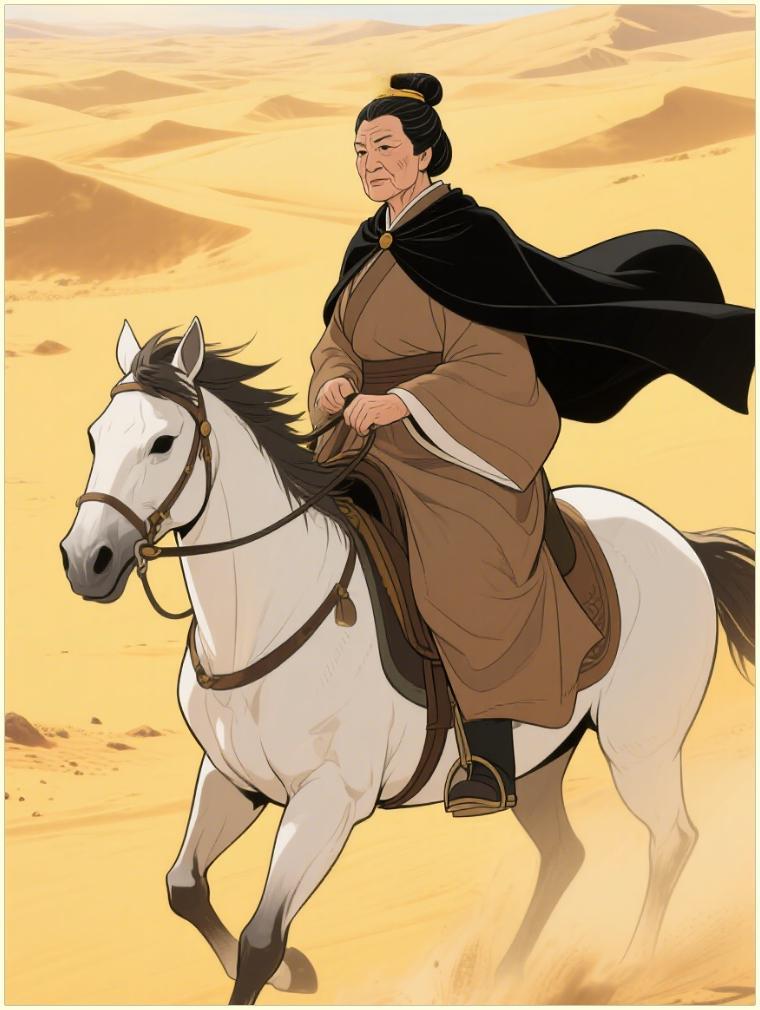
(大遼太后 述律平)
趙思溫十分巧妙的使用了歸謬法,也就是反證,他的反脣相譏,他的反問,其實本質是在通過接受對方理論的前提上,推導出自相矛盾的結論,從而再次推翻對方的理論,這一招那就很厲害了。
不過,述律平絲毫不慌,趙思溫說完,述律平的回答是:
我並非不想要追隨先帝於地下,只是因爲皇子們尚且年幼,需要人照顧,新帝又剛剛登基,難以獨自處理國事,所以我還不能赴死。
這話,說的非常牽強,很難強而有力的還擊趙思溫,但是接下來,述律平做了一個十分驚人的舉動,她突然撿起一柄快刀,手起刀落,直接把自己的左手給砍了下來,然後命人放進了耶律阿保機的墓中。
意思是,雖然我不能自裁,不能親自去陪伴先帝,但是我把一隻手砍下來放到先帝墓中,以手代身。
斷手,或者我們說是斷腕,其實是一種物理自殘,述律平通過這樣的行爲,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還轉移了矛盾的焦點。
怎麼着?我手都斷了,你趙思溫還有什麼話說?
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有一位女法老,名字叫做克利奧帕特拉七世,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埃及豔后,述律平的斷腕,正好和埃及豔后之死形成了奇妙的鏡像,西方女主以毒蛇終結屈辱,東方女主以肉身還以顏色,她們的存在,共同揭示了女性統治者在男權世界的殘酷生存法則。
可以說,述律平什麼大風大浪沒經歷過?趙德均這樣的宵小之輩,她根本就不放在眼裏。
趙德均拜見了述律平之後,述律平問他,你本來駐紮在河北,爲什麼卻帶兵到了山西一帶。
趙德均說,此前奉了後唐皇帝的命令,要征討石敬瑭,同時還要抵抗契丹的軍隊。
述律平是一聲冷笑,說你胡說八道,你這種不忠不義的人,根本就沒想過要報效國家,你只是想要投降我們契丹罷了,你能欺騙你的主君,你能欺騙我們的契丹皇帝,甚至你能欺騙我,但是你能欺騙你自己的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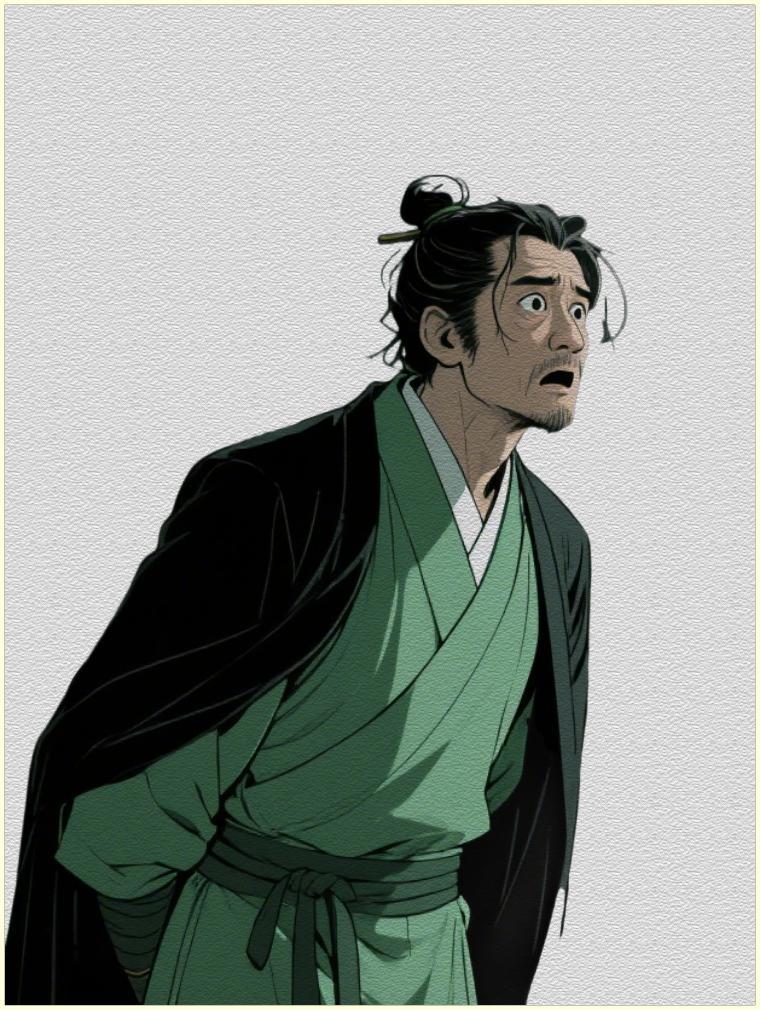
(後唐降將 趙德均)
述律平是越說越生氣,他痛斥趙德均不仁義,不仗義,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和主公,說他沒有氣節,說他趁着家國內亂,想要趁火打劫,說他幹出這樣的醜事來,怎麼還有臉面,還好意思活在這個世界上?
想一下,事實上自從唐末五代戰亂以來,中原漢地,投誠於契丹人的文官武將並不少,很多漢人官員,漢人將領甚至都成爲了契丹國家的中堅力量,這說明契丹統治者對於中原而來的士子和武人並不排斥,那爲什麼述律平會對趙德均如此的厭惡,如此的嗤之以鼻呢?
原因在於,很多在契丹任職的漢人,他們之所以會來到契丹,很大一部分是因爲戰亂流離,無處可去,或者是在政治中的失敗者,失意者,爲了求生,他們纔來到了北方,他們遠離故國的理由不一定完全合理,但是肯定要比趙德均合理。
趙德均鎮守幽州多年,他早不投契丹,晚不投契丹,沒有在契丹微弱的時候就投奔,而是在契丹大軍壓境,後唐式微之際才選擇倒戈相向,在契丹人看來,他的投誠非常沒有誠意。
而且,趙德均既沒有徹徹底底的盡忠於後唐,也沒有像石敬瑭那樣孤注一擲的投靠契丹,而只想要在夾縫中獲得漁翁之利,所以趙德均在述律平的眼中,不是像石敬瑭那種帶來巨大利益,擁有明確立場的投靠者,也不是韓延徽那種帶着忠誠和力量來歸附的建設者,這個趙德均,實則混到這一步,他是一個走投無路,毫無價值,只配被唾棄的失敗投機者。
因此,述律平對他的鄙視和厭惡,遠超過對一般敵人或普通降將的態度,這是一種基於其行爲本質的,深刻的道德和價值判斷上的否定。
面對述律平的質問和批評,趙德均無話可說,他惶惶告退,回到家之後羞愧不已,不久後就病死了。
朱門車馬卷紅塵,蟻陣附炎來往頻。
槐下衣冠爭腐鼠,不知皆是弈枰人。
當年也是響噹噹的北平王,如今落到這一步,歷史只會送給趙德均四個字:
咎由自取。
趙德均失敗退場,石敬瑭終於放心了,天福元年,公元936年,石敬瑭在山西太原稱帝,成爲了後晉的開國皇帝,不久之後他帶兵攻入洛陽,李從珂自焚而死,後唐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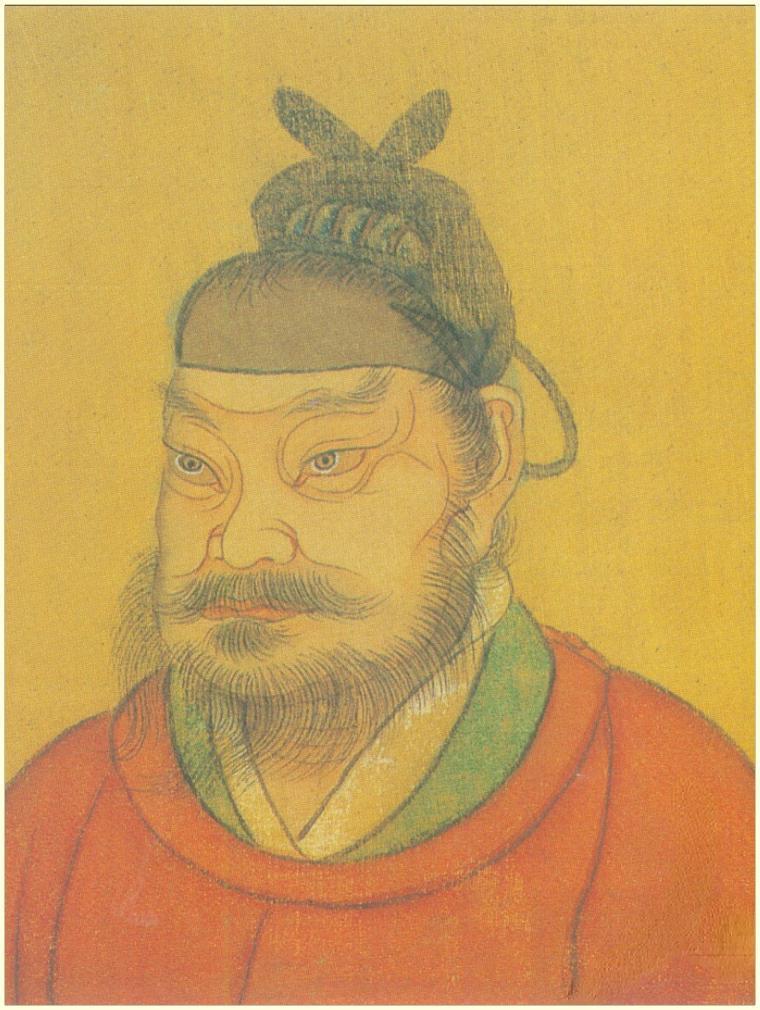
(石敬瑭)
李從珂自焚,其實也只僅僅是燒了一個玄武樓,洛陽的城建大部分都還在,而且洛陽一直以來的發展就不錯,石敬瑭完全可以繼承後唐的城市遺產,將後晉的都城建立在洛陽,但是石敬瑭沒有這麼做,他很快就把都城遷徙到了開封。
這個遷都的舉動,不太好評價。
開封在汴河和黃河的交匯處,是隋唐大運河的核心節點,通過汴河,可以快速便捷的連接江淮地區,江南的糧食啊,物資啊,就可以源源不斷的運到中原來。
洛陽就不一樣了,洛陽雖然也有洛水,可是漕運需要通過三門峽這道險關,運輸的效率很低不說,風險還比較大。
因爲五代就是不斷的戰亂嘛,打仗很頻繁,在這種環境中,一個政權的都城需要穩定的物資供應,開封依託運河網絡,就可以更好的獲取江南地區的財富。
其實上我們再深入思考一下,石敬瑭是在契丹人的扶持下稱帝的,把燕雲十六州割讓出去之後,整個中原就會直面契丹騎兵的威脅,我們說既然有威脅,那就應該離的越遠越好,正常來說,開封地處平原,無險可守,又離契丹更近,選哪裏做都城也不會選開封做都城,但是石敬瑭偏偏遷都開封,他直接就把自己暴露在了契丹的攻擊範圍內,這其實體現出了石敬瑭的一種心態,那就是他建立後晉之後,他是沒有意圖,也沒有心思和契丹把關係變成敵對狀態,他也認爲契丹絕對不會攻打他。
在石敬瑭的意識裏,後晉的存亡完全取決於契丹的態度,如果契丹有一天想要滅晉,別說躲到洛陽了,就算是躲到長安也難逃一劫,既然如此,還不如主動示弱,換取契丹的支持和信任。
又何況,自己割地稱臣,引狼入室滅亡後唐的行爲,並不能得到前朝公卿百官士大夫的積極支持,就算是爲了避開後唐的舊勢力,遷都也是勢在必行。
對於他這樣的行爲,作者無話可說,也懶得再說。
趙德均在契丹身敗名裂了,石敬瑭雖然在開封登基,做了皇帝,但是他失去了燕雲十六州,失去了天下人的支持,失去了中原的屏障,兩人同以屈膝換權位,所以看似殊途,實則同歸,當石敬瑭穩坐開封城放眼天下之時,他以爲塵埃落地,卻不知道,棋盤遠未終局。
屈膝賄禍,終噬臍膺,失道寡助,天道好還。
亂世如熔爐,淬鍊英雄,更焚盡宵小,昨日引火燒身的是他李從珂,誰知道今日明日後日,是不是就輪到你河東石郎了呢?
參考資料:
《遼史·卷七十一》
《契丹國志·卷十三》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柳宗書.斷腕太后——述律平.百科知識,2015
郭平.三位蕭太后在遼代先後執掌朝政.遼寧日報,2022
稅玉婷.耶律阿保機的情感生活與遼初政治.赤峯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