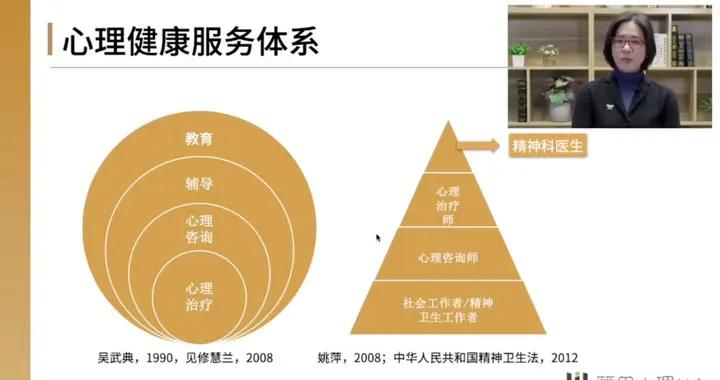前幾年網劇《贅婿》的熱播,一度掀起一股入贅的風潮,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男生都半開玩笑似的開始往這方面靠攏了:
網上不乏有男生表示自己“不想再奮鬥了”,想找個家庭條件出衆的妻子當“贅婿”。
同時其實也可以發現人們對於“贅婿”身份和現象的接受閾值已經愈發正常。
當然,大部分男性對於“入贅”這樣的詞彙還是有些牴觸的。這就要從這種行爲本身說起了。
無論是“入贅”、“倒插門”還是“上門女婿”,在傳統社會中指的是丈夫婚後到女方家中生活;
孩子隨女方姓、任勞任怨,部分地區還要兼具幫女方家庭生育子女、添丁進口的職責。
這在之前的社會觀念中代表着脫離家庭、失去尊嚴,所以除了不用花彩禮之外,“入贅”幾乎得不到認可。

但是在浙江蕭山,有這樣一個婚介所,專門幫助那些想當“贅婿”、不介意做“上門女婿”的男性介紹婚事,甚至在業界還有很高的聲望。
在如今大齡單身男性人數居高不下的環境下,更是有不少客戶不遠千里坐高鐵前來,花費上萬的介紹費,只爲尋求一個合適的“妻家”。
婚介所的“所長”李繼延對此只是淡淡一笑——時代變了,尤其在蕭山這樣一個地區;
一般家中有女兒的,條件有不錯的,都希望女兒在婚姻中也更加主動、有地位,甚至有人將蕭山地區成爲“贅婿核心地帶”。
對於當下的入贅現象,其實主要涉及到的是幾重張力:
首先,“入贅”背後是倫理張力。傳統“男娶女嫁”屬於父權婚姻倫理,本質在於以丈夫爲中心,進行代際和財產的延續;

而“女娶男嫁”的入贅模式則屬於將妻子置於男性位置上,通過付出財富實現下一代的傳承。
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無論是“娶”還是“嫁”,目的都是以資本更加強勢的一方爲尊,以一定的支出(彩禮)獲取下一代綿延的機會。
當下有部分女性會糾結“冠姓權”,其實即便是隨母姓,網上追溯也是隨外公姓,本質上仍然屬於父權制範疇,沒有太大區別。
所以如果部分男性真的想得通,入贅對他們而言也不是倫理上真的不能接受的。
其次,婚姻也是資本交換的場域。
正如上文所說,很多男性之所以相當“贅婿”,很大的目的是“不想努力了”,也就是將原本的面子、身份拋之腦後,將資本拿到手中。

一般而言,招婿是需要女方家庭出具彩禮等一系列資金的,但男性“嫁”過去之後,幾乎可以說是喪事一切經濟權力:
收入盡數上繳(如果有收入)、只留生活費。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尤其是蕭山地區的部分男性,寧願爲了房產、生活水平、社會資源等,而成爲“上門女婿”。
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傑爾(Alfred Gell)將之稱爲“物的魅惑”(the enchantment of technology):
當房產、彩禮等物質被賦予了一定的行動能力,其當然會反過來操控人的行爲。所以如果非常缺錢,又不在乎身份,當“贅婿”不失爲一種選擇。
同時,入贅之後的生活還包含各種權力的張力。
上文所說的失去經濟權力只是其中一部分——畢竟婚後上交工資卡的人也不在少數。
除此之外,入贅意味着長期生活在岳父岳母家中,並且以他們爲尊。
這也使得部分“贅婿”出現不同的面孔:在丈母孃面前十分乖巧懂事,回到家中,在父母面前又要繃足面子,表示自己“過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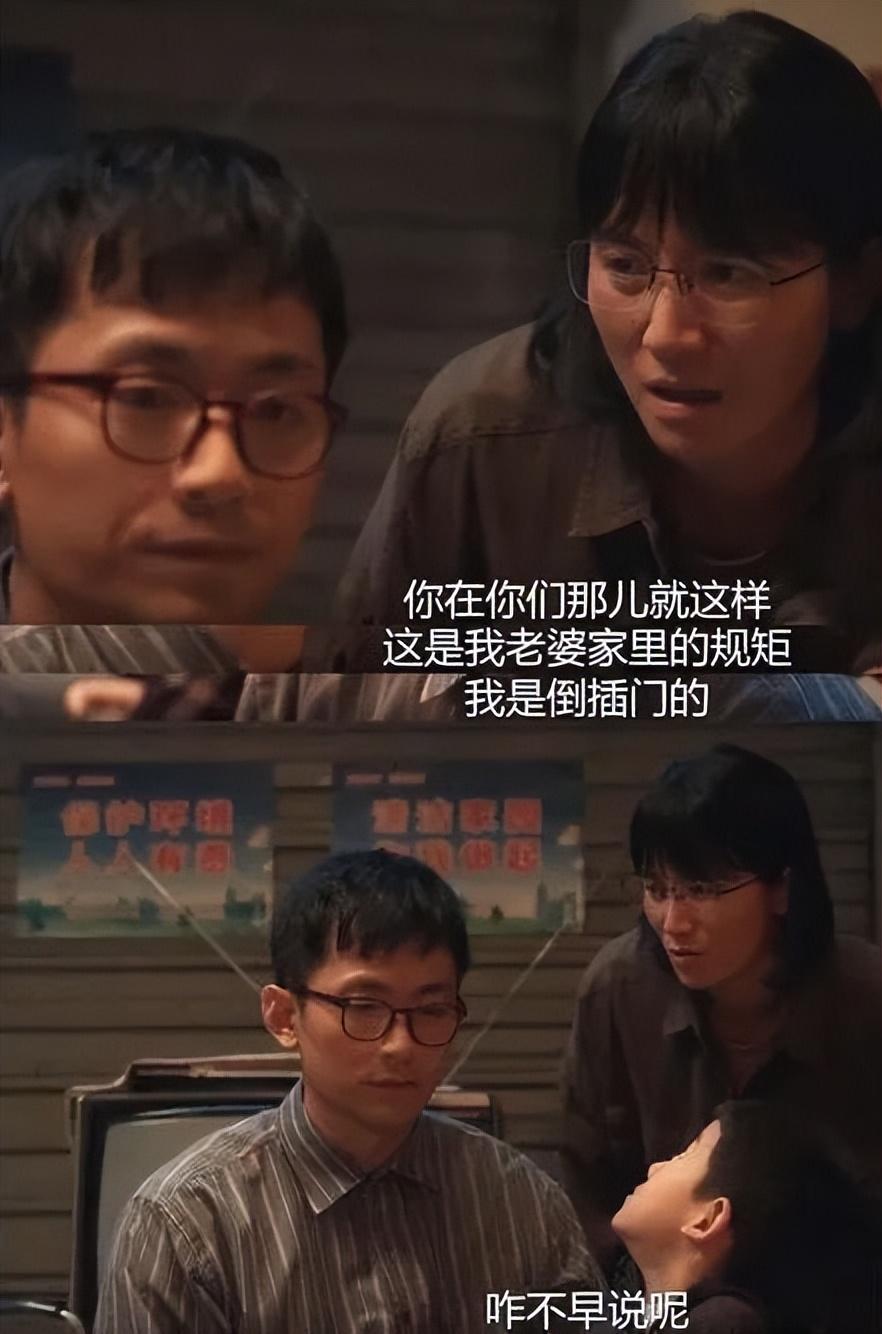
在心理學家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看來,這屬於比較典型的“虛假自我”現象;
這是一種戴着面具生活的夾縫之道,隱藏着被壓抑的需求與不如意的現實生活導致的不滿。
最後,“入贅”在社會生活中更多的還是個身份問題。成爲“上門女婿”之後,難免還會有其他的關係和交往:
不論是回到原生家庭還是和同事、朋友接觸,提起“贅婿”,可能更多人都會流露出一種“懂的都懂”的戲謔表情。
對於“贅婿”本人而言,婚姻是一時的決定,但在漫長的人生中,可能每一次涉及到當年的選擇,內心都會遭到衝擊。
如果心智不夠成熟,那麼對於入贅這個選擇最好還是慎重。

從蕭山地區的“贅婿”現象來看,我們處在現代社會和傳統觀念交融的社會狀態;
像前來婚介所爭當“贅婿”的這些男性而言,他們的內心可能也充滿了倫理、資本、權力和身份等的多重博弈。
-The End -
作者-木易
第一心理主筆團 | 一羣喜歡仰望星空的年輕人
圖片源自網絡,侵權請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