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些痛苦,並不是一段時間的低谷,而是貫穿從青春、壯年到老年的持續反覆的陰影。今天我們故事中的主人公,便是如此,五十年來,他看過無數醫生,喫過無數藥,輾轉不同的城市,也在一次次“好轉—復發—再好轉”的循環裏步入退休後的時光。直到七十多歲,才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也許自己不是“治不好”,而是從未真正被理解、被接納過。這是汪先生的故事,一位與抑鬱症抗爭半個世紀的退休教師,在暮年重新找回內在秩序與生命尊嚴的故事。
01
他的抗爭,從一場被中斷的青春開始
如果不是汪先生自己告訴我們,很難想象,這樣一位聲音洪亮、思路清晰的老人已經七十九歲了,而且竟然已經與抑鬱症對抗了整整五十年。
他的人生,本該有一條截然不同的軌跡。十八歲那年,他考入一所當時在省內頗有名氣的重點中學,那一屆學生,很多人的志願都是上“北大”、“清華”,包括汪先生本人在內,他們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可命運在 1966 年爲他的夢想按下了暫停鍵,高考取消,汪先生和同齡人一起,被時代裹挾着回到鄉村,青春沒有正式告別,就戛然而止。
他回到農村,務農、勞動。看上去他積極適應;可內心深處,一種說不清的失落與壓抑,正在悄然積累。那時候,沒有人知道什麼是抑鬱症,也包括他自己。

02
第一場發作——沒有名字的痛苦
二十多歲時,汪先生開始出現明顯的症狀,情緒低落、對生活失去興趣、睡眠嚴重受損、整個人像被抽空了一樣。
後來,鄉鎮中學缺老師,他成爲了一名當民辦教師,教學工作讓他暫時有了事做,症狀似乎也短暫地緩一緩,但還是爆發了,最嚴重的時候,一次發作會持續兩三個月。他說:“那種感覺,就是生不如死。喫不下飯,睡不着覺,連洗臉、刷牙都需要極大的力氣。” 而最更讓人難受的,是不被理解。在那個年代,這些都不會被稱爲“心理困擾”,親戚、鄰里、甚至一些家人都無法理解,人們只會批評他想不開,或者勸解說歇歇就好了。
甚至他自己也一度這麼認爲。

03
漫長的求醫路——藥物、專家、反覆失望
後來幾十年裏,汪先生幾乎把所有可能的方式都試過。先是當地和省內的各大醫院、後來又輾轉到上海掛專家號,在那個年代,一次專家門診最貴的甚至要800塊錢,這對一個普通家庭來說,是極其沉重的負擔。可即便如此,他還是一次次嘗試。
然而藥物能緩解,卻無法真正穩定,停藥後復發幾乎是必然。特別是到每年春天,病情就會再次復發。他曾絕望地想:“這種病,也許只能自己扛。”
04
退休之後的危機和轉機
終於到了六十歲退休,原本以爲也許一切會慢慢轉好,可對汪先生來說,卻迎來了更大的挑戰。身份的轉變,原本還能被“責任”和“事務”支撐着的心,突然空了,心中的痛苦反而佔據了更大的空間。有時一年發作四次,身體虛弱,精神低落,整個人像被反覆碾壓。經過這五十多年的折磨,他幾乎已經接受了這樣的人生——可能這輩子,就這樣了。
然後命運最終沒有辜負他一生的堅持和抗爭,轉機在他七十多歲時,雖然很晚但終於到來。他偶然讀到李宏夫老師撰寫的《戰勝抑鬱》一書,第一次看到一種以“覺察、接納和平等心”爲核心的理解方式,他開始嘗試書中的練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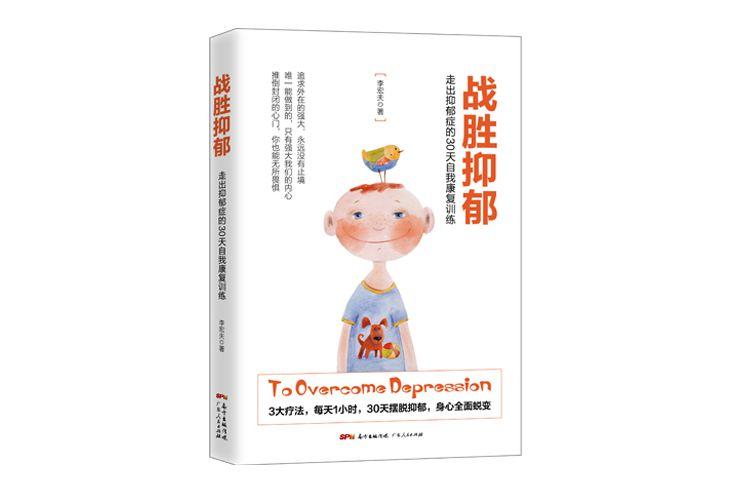
一開始,並不熟練,也沒有老師指導,只能自己摸索。後來,他通過書上的聯絡方式加入了李老師的讀書會和共修營。此後,他再也不是獨立面對和承受這一切,他聽到別人講述的經歷,才知道原來自己不是怪,原來這麼多人都在這樣同一條路上摸索。
讓我由衷敬佩的是,汪先生以七十多歲高齡,每天早晚堅持靜坐觀呼吸練習,他重新獲得了一種內在的秩序感。他笑得很爽朗,告訴我:“我現在精神比以前好多了,如果年輕時就有人告訴我這些,也許會少走很多彎路”。但他並不怨恨,也不否認過去的痛苦,而是坦然接受過去的一切都不會白白經歷。
現在的他在生命的後半程,終於體驗到了一種久違的安穩。
汪先生用一生的經歷在告訴我們,即使被抑鬱陰影籠罩半個世紀,我們依然有可能重新找回內在的秩序、尊嚴與平靜。這也是對所有仍在黑暗中行走之人的回答,你沒有走錯路,不要灰心、要有信心,有時可能只是需要走得久一點。





